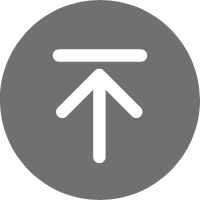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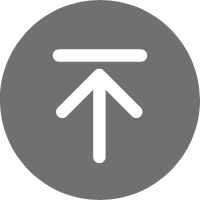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当艺术团队Obvious利用生成对抗网络生成的肖像画Edmond de Belamy在佳士得拍得43.2万美元的时候,当音乐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组建的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将贝多芬设想的《第十交响曲》变成现实的时候,当徐冰和他的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电影参加平遥电影节的时候,人工智能艺术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产品能够算作艺术吗?人工智能艺术与人类艺术有什么关系?人工智能艺术与人工智能产品有什么不同?人类需要人工智能艺术吗?诸如此类的根本性问题,是今天的美学和艺术学必须处理的难题。为了确保关于人工智能艺术的讨论在美学和艺术学的范畴之内,我们可以参考20世纪后半期环境美学家处理自然审美问题的做法。一项在自然、艺术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艺术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
一、范畴感知与肯定美学
20世纪后半期环境美学得到极大发展,与艺术定义理论和日常生活美学一道,成为当代美学三大重要议题。为环境美学从美学边缘进入中心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学家,非卡尔松莫属。为了确保对自然的讨论在美学的范围之内,卡尔松提议该讨论参考美学家对艺术的讨论方式,因为对艺术的讨论被奉为美学的经典内容,以致美学可以等同于艺术哲学。
关于艺术的审美欣赏,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学说,卡尔松将瓦尔顿的范畴感知理论作为范例。瓦尔顿认为,我们需要将艺术放在与之相应的范畴下进行审美欣赏。例如,要谈论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就需要将它放在“立体派”的范畴下来感知。将《格尔尼卡》放在“立体派”的范畴下来感知,它就会被评判为一件伟大的作品,即一幅伟大的立体派绘画;如果将它放在“印象派”的范畴下来感知,它就会被评判为一件拙劣的作品,即一幅拙劣的印象派绘画;如果将《格尔尼卡》放在“绘画”甚或“艺术”的范畴下来感知,人们就很难得出准确的评价,既可以说它是伟大的,也可以说它是拙劣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应该被放在“立体派”而非“印象派”范畴下感知,应该被评价为一件伟大而非拙劣的作品,这是由美学家、艺术学家、艺术家本人以及艺术界公众等共同决定的。这就是瓦尔顿范畴感知理论的主要内容。
卡尔松主张,为了确保关于自然审美的讨论在美学的范围之内,需要参考瓦尔顿关于艺术的范畴感知理论,也就是说需要将自然物放在与之相应的范畴下来感知。如果一般地将自然物(例如大熊猫)视为自然,就像一般地将艺术品(例如《格尔尼卡》)视为艺术一样,我们就很难对它作出适当的感知进而作出准确的评价。只有将自然物(例如大熊猫)放在与之相应的范畴(例如哺乳动物)下来感知,我们才能对它作出适当的感知进而作出准确的评价,就像将艺术品(例如《格尔尼卡》)放在与之相应的范畴(例如“立体派”)下来感知和评价一样。至此,卡尔松的自然审美与瓦尔顿的艺术审美完全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卡尔松接下来的推论也会与瓦尔顿一样。
卡尔松的自然审美理论与瓦尔顿的艺术审美理论的最大不同,在于范畴的确立和应用方式不同。就艺术来说,范畴是艺术学家确立的,艺术家在艺术学家确立的范畴下进行创作。就自然来说,范畴是科学家确立的,但是自然不会在科学家确立的范畴下进化。由于艺术家是在艺术学家确立的范畴下创作,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有可能因为符合范畴的要求而被评价为成功的或者优秀的,也有可能因为不符合范畴的要求而被评价为失败的或者拙劣的。但是,自然物与艺术品不同。自然物不是人造的,科学家也不能创造自然。科学家的创造与艺术家的创造刚好相反:科学家为业已存在的自然创造范畴,艺术家在业已存在的范畴下创造作品。艺术家创造的目的是让作品尽量符合范畴的要求,科学家创造的目的是让范畴尽量符合“作品”(如果说自然也是作品的话)的实际。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有因可能不符合范畴的要求而被认为失败的或者拙劣的,但是自然不会因为科学家创造的范畴不符合它的实际而是拙劣的,自然只会因为科学家创造的范畴不符合它的实际而隐匿不显。科学家为自然创造范畴的目的,就是让自然完美无缺地显现出来,完美无缺地被我们认识。自然要么完美无缺地显现,要么不显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卡尔松主张自然全美。也就是说,自然在科学家为它量体裁衣式地确立的范畴下显现得完美无缺,这就是卡尔松的“肯定美学”。
卡尔松还设想了一种像科学家一样工作的艺术家,也就是所谓的天才艺术家或者划时代的艺术家,他们不仅创造作品,而且创造适合自己作品的范畴。例如,毕加索不仅创造《格尔尼卡》,而且创造适合感知《格尔尼卡》的“立体派”。正因为“立体派”是为了更好地感知毕加索相关作品而创造出来的,毕加索的相关作品才总是显现为完美的立体派作品。毕加索为自己相关作品量体裁衣创造“立体派”范畴的工作,类似于科学家为自然量体裁衣创造范畴的工作。当然,毕加索创造的“立体派”范畴必须被艺术界接受才能发挥效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科学家的理论必须被社会接受才能发挥效力一样。
二、无范畴感知与否定美学
尽管瓦尔顿的范畴感知理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但它未能揭示出审美和艺术的特征,因为它将审美和艺术混同于一般认知和人工制品。的确,我们要将事物放在与之相应的范畴下来感知,才能获得关于它的中肯评价。比如,如果我们将电动汽车放在马车甚或油车范畴下来感知,就不能获得关于它的中肯评价。这种范畴感知适用于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因而不能将审美和艺术的独特性揭示出来。审美与认知的区别、艺术与寻常物的区别,刚好就在于审美和艺术抵制范畴感知,而认知和寻常物服从范畴感知。在康德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是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静观。朱光潜用木商、植物学家和画家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对此做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尽管木商、植物学家和画家三人都知觉到古松,但是他们所知觉到的结果却非常不同:商人离不开商人的习惯,“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植物学家离不开植物学家的习惯,“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画家则“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这三个人在知觉之后的反应也很不一样:木商“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么去买它,砍它,运它”;植物学家“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如何活得这样老”;画家“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是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在朱光潜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将木商的知觉视为有目的的知觉,将植物学家的知觉视为有概念的知觉,它们都是有利害的,只有画家的知觉是无目的、无概念因而是无利害的。作为审美之标志的无利害静观,不是有范畴的感知,而是无范畴的感知。这正是审美能够与认知和道德活动区别开来的关键。尽管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不少美学家反对将审美建立在无利害的静观之上,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利害静观,但是不能因此就反过来将认知和道德所依赖的范畴感知视为审美的特征。虽然不能将概念完全排除在审美之外——在审美的某些阶段(例如准备阶段或者训练阶段)的确需要依据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与认知相比,审美更少依赖概念,有可能在某些阶段(如高潮阶段)完全不需要概念,或者说概念完全内化在感知之中。就像青原惟信的修行三境界说所表达的那样,到了最后的“见山只是山”的阶段,知觉就完全不依赖概念,或者说概念完全内化在知觉之中了。总之,无论如何,与求知和向善活动相比,审美是较少依赖概念的。范畴感知只是求知和向善活动的特征,而不是审美活动的特征。这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心胸理论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达。
与瓦尔顿和卡尔松针锋相对,笔者将无范畴感知视为审美的特征,不仅指艺术审美,而且包括自然审美。在笔者看来,艺术品和自然物之所以比寻常物或一般人工制品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原因在于艺术品和自然物抵制范畴感知,而一般人工制品迎合范畴感知。一般人工制品之所以迎合范畴感知,是因为一般人工制品是依据范畴制作出来的。电动汽车是依据电动汽车的范畴制作出来的,只要完美地符合电动汽车的范畴,就会被判定为质量过关。
但是,自然不是依据任何范畴制作出来的。科学家的范畴尽管是为自然量体裁衣式地构造出来的,还是不能完美地符合自然的实际,正因为如此,科学家才会不断修正范畴。如果自然完美地符合科学家为它量体裁衣制作出来的范畴,科学范畴就无须修正,因而就不存在科学的进步。科学不断进步的历史恰恰表明,任何特定历史阶段人类为自然量体裁衣制作的范畴都不能完美地符合自然,都会遭到自然的抵制。自然在审美上的魅力,刚好就在于它有溢出范畴感知的部分。如此,阿多诺才会认为自然物保留着“非同一性”的残余。
同样,艺术的魅力也不在于它符合范畴,而在于它抵制或者溢出范畴。康德明确指出,艺术,即所谓美的艺术,就是天才的艺术。“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由于这种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在康德看来,只有天才艺术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其他的都是迎合社交乐趣的艺术或者一般人工制品。鉴于天才是天生的内心素质,所谓天才艺术就是按照艺术家的自然本能来创作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仅没有范畴,而且不遵循规则。如果说艺术有什么规则的话,天才就是艺术的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只有具体的榜样,没有抽象的规则或范畴。因此,我们不能依据是否符合规则或范畴来判断艺术的优劣。康德美学对随后的浪漫主义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浪漫主义艺术强调创造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对外在规则或范畴的遵循;艺术是完全自律的,既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提升,而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即艺术与现实完全无关。因此,我们不能依据现实世界的规则和范畴来感知和判断艺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不乏类似的见解。例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别材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天才。当然,严羽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西方浪漫主义美学中的天才指的是天生素质,跟读书穷理无关。中国传统美学不支持这种天生的天才观,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来说,不是不要读书穷理,而是要多读书、多穷理,通过多读书、多穷理来超越书和理。再一次借用青原惟信的话来说,浪漫主义美学的天才观相当于第一境界即“见山是山”,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别材观相当于第三境界即“见山只是山”。总之,无论是本来的没有范畴,还是后来的超越范畴,对艺术的审美感知都与范畴感知无关。
由此,与一般人工制品遵循“同一性”不同,艺术与自然体现出“非同一性”的特征。艺术和自然在审美上的魅力,不是因为它们符合相关范畴,而是因为它们抵制任何范畴,它们总是溢出范畴的笼罩而顽强地显现自身。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庄子的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论证了一种与卡尔松的肯定美学针锋相对的美学,笔者将它称作“否定美学”。这里的否定指的是对范畴的否定,不是对审美价值的否定。
三、人工智能与技术
在澄清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后,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审视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框架。人工智能尚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艺术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根据高峰的观察,今天的计算艺术或人工智能艺术已经由1.0阶段进入2.0阶段。“在1.0阶段计算艺术构成了人机共创范式的雏形……为后续人工智能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程序思维’与‘自动生成’这两大核心美学基石……在计算艺术2.0阶段,创作模式由传统的程序控制范式转向人机共创的交互机制,艺术家通过提示词(Prompt)与人工智能进行动态互动,从中激发灵感并引导生成过程。”1.0阶段和2.0阶段的人工智能艺术会表现得非常不同。
同时,鉴于艺术既可以是分类概念,也可以是评价概念,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艺术有可能指的是非常不同的事物:一种是艺术家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的作品,另一种是人工智能独立完成的作品。在现阶段,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艺术家以人工智能为工具生产的作品,人工智能独立完成的作品尚未出现,但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且,这两种人工智能作品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以人工智能为工具生产的作品中多少包含着人工智能独立完成的部分。但是,人工智能艺术是否真正的艺术呢?这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以肖像画Edmond de Belamy为例。这幅“绘画”之所以被视为艺术,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创作者Obvious团队想要把它做成艺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被拍卖行接受并被成功拍卖。第一个涉及艺术的意图条件,第二个涉及艺术的接受条件。根据艺术体制理论,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归入艺术之列。但是,在这里人工智能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如果我们要遵从艺术体制理论将它视为人工智能艺术,就要证明人工智能与意图和接受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在艺术体制理论的框架下来讨论人工智能艺术。
Obvious团队(我们权且称他们为艺术家)之所以要利用人工智能,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人工智能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意图。如果艺术家的意图被完美地实现,其结果能否称作艺术呢?按照许多美学家的观点,其结果当然可以称作艺术。但如果人工智能只是帮助艺术家更快、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意图,即使最终创作出来的作品算作艺术,也难以称得上是“人工智能艺术”,因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人工智能承担的只是执行部分,而不是创意部分。在崇尚观念创意的当代艺术领域,执行部分可以被忽略不计,就像勒维特所说的那样,“观念或概念是作品最重要的方面。当艺术家采用观念形式的艺术时,这就意味着所有计划和决定都是事先作出的,具体执行并非重要事情”。
当然,Obvious团队采用人工智能的目的,一定不只是更快地实现他们的意图。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绘画就跟一般产品生产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符合意图并非艺术创作的充分条件,而是人类行为的一般特征。对于一些美学家来说,符合意图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艺术。科林伍德就持这种看法,他主张艺术创作不受意图的约束,完全符合意图的只是巫术或者娱乐,而非真正的艺术。在科林伍德看来,真正的艺术不是再现,而是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具象绘画就不是艺术,抽象绘画才是艺术。科林伍德说:“一座大楼或一只杯子,首先是一件人工制品或工艺品,却也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但是,使它成为艺术品的原因不同于使它成为工艺品的原因。一个再现物可以是艺术品,但是,使它成为再现物的是一种原因,而使它成为艺术品的却是另一种原因。”这里涉及科林伍德对再现和表现的独特理解。简要地说,只要艺术家在创作之前知道自己要创作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只要创作出来的结果符合艺术家的构思或者意图,那么这种创作就是再现;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之前不知道自己要创作的东西,只是因受到压抑而产生释放的冲动,他的创作只是释放他的冲动,无论创作出来的结果是具象绘画还是抽象绘画,都是表现。总之,再现的对象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在艺术家头脑中,第二次是以任何一种媒介将头脑中的对象传达出来。表现的对象只出现一次,无论是在艺术家头脑中还是在具体的媒介中。如果在艺术家头脑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对象,艺术创作就业已完成,无须用媒介将它外现出来;如果在艺术家头脑中没有明确的表达对象,对象只是在媒介中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对象就只存在一次,即在媒介中存在。这是科林伍德表现论的要点。因此,如果艺术家借助人工智能实现他头脑中明确的意图,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其结果就不是真正的艺术,而是娱乐或者巫术,人工智能的作用只不过是提高生产效率而已。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只是艺术家使用的工具,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艺术家必须发出明确的指令,甚至艺术家只是在人工智能允许的范围内勾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尽管可以完美符合艺术家的意图,也不能算作科林伍德意义上的真正的艺术。从Obvious团队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的肖像画Edmond de Belamy来看,它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完美的肖像画。它被拍卖行接受并且拍出不菲的价格,绝不是因为它像任何意义上的完美的肖像画。
将艺术家使用人工智能的目的理解为方便实现自己的意图,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或许艺术家采用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意图,而是产生意外的效果,即生成艺术家难以控制的作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艺术性就有可能体现出来。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艺术家借助人工智能让自己的创作介于科林伍德所说的再现与表现之间,从而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性。在这里人工智能起到的作用是阻隔作用,它能改变艺术家的意图,生成艺术家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艺术家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情况是这样的:艺术家事先有明确的想法,由于人工智能也有它自己的“想法”,艺术家在与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致使最终产生的结果完全超出了艺术家最初的预想。从最终的结果与最初的想法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人机共同生成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林伍德所谓真正的艺术要求。但是,这里仍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果艺术家在跟人工智能对话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想法,这些想法以家族相似的形式使最初的想法与最终的想法完全不同,尽管最终结果与最初想法完全不同,也不能算作科林伍德意义上的真正的艺术。因为科林伍德更重视创作时的心灵状态,即由压抑到释放的过程。在那个设想的家族相似关系中,每个阶段都没有由压抑到释放的转化。总之,按照科林伍德的理论,艺术创作类似于“黑箱”,它不能诉诸理性的解释。在人工智能作为艺术家的工具实现艺术家的意图时,这个黑箱是不存在的。在艺术家经过与人工智能的系列对话而改变意图的特例中,“黑箱”被分解为一系列阶段,从而也不再是完全封闭的“黑箱”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处理所谓的“涌现”或者突变了。不少人谈到人工智能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涌现现象,尽管这种突变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但笔者仍然没有把它归入人工智能的自动创造,因为这种涌现仍然是在艺术家提示词的引导下出现的。就像经过家族相似,艺术家最初的意图与最终的结果完全不同仍然不能算作表现一样,人工智能的涌现也能用家族相似来解释,它是在经过若干环节之后出现的突变或者意外,如果将这些环节联系起来,这些突变或者意外仍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出现了完全超出艺术家意图的结果,即使出现了人工智能的明显的涌现,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产品也不一定被接受为艺术,它也有可能被认为是科学发明。
那么,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产品如何才能被认定为艺术呢?这里我们就从艺术意图转移到了艺术范畴。我们是根据已有的范畴来判断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产品是否艺术:符合范畴的就是艺术,反之则不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跟卡尔松和瓦尔顿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符合范畴的不一定是艺术,也有可能是一般的人工制品。人工智能生成的Edmond de Belamy符合肖像画,我们称之为艺术;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符合城市规划图,我们就会称之为技术性图片而非艺术。这里的符合其实是一样的,人工智能的自主生成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根据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将其结果判断为艺术,而是根据符合艺术范畴将人工智能创作的结果判断为艺术。但是,符合范畴并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要成为艺术有时候更需要突破范畴,抵制我们的范畴感知。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了一个不符合任何范畴的东西,那么它是否艺术呢?在毕加索那个例子中,毕加索创作出了超出以往任何艺术范畴的绘画,但是仅仅凭借全新的特征,他的绘画还不能算作艺术,他还需要创建适合理解其作品的范畴即立体派,而且立体派范畴需要得到艺术界的认可。如果人工智能涌现出一幅全新的“绘画”,这幅绘画很有可能不被视为艺术,甚至不被视为绘画,除非人工智能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创造出了相应的范畴和理论,且被人类艺术界所接受。在目前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显然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当然这也不在人工智能的任务清单之内,因为人工智能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艺术。总之,如果从现有的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产品很难算作艺术。
就肖像画Edmond de Belamy来说,它不是简单地因为被拍卖行接受并拍出高价而成为艺术。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能够被拍卖行接受并拍出高价?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人类对肖像画的理解:它的确看起来像一幅肖像画,但又不像任何人类手绘的肖像画。然而,对肖像画的理解不是人工智能作出来的,而是人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只是生成了一张图片,人类根据艺术界的惯例将它视为肖像画,视为艺术。
四、人工智能与自然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通过人工智能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看它生成的产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如果具有审美价值,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将它视为艺术。
在讨论人工智能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没有涉及人工智能的独立创作,笔者认为目前这个时刻还没有来临。假定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全可以实现自主创作,我们如何来看待它生成的产品,它们可以被视为艺术吗?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被视为艺术?
如果人工智能完全自主创作,它生成的产品就像自然物一样。将人工智能的生成理解为自然造化,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用卡尔松的环境美学范式即范畴感知来理解人工智能产品的审美问题呢?在卡尔松的环境美学范式中,科学家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自然的范畴,而且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具有很长的历史、积累了很多知识,因而具备提供范畴的能力。但是,对人工智能生成的产品,人类并没有相关研究,因而无法提供范畴感知所需要的范畴。我们可以用人类已有的关于自然、艺术和社会事物的范畴来理解人工智能产品,但是鉴于这些范畴本身不是针对人工智能产品而设置的,用它们来理解人工智能产品就难免发生误解和错位。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人工智能不仅生成产品,而且能像天才艺术家一样生成理解产品的范畴,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范畴能否为人类所理解和接受,仍会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作为人类,笔者不希望人类接受人工智能的规训,也不希望人类完全被自己发明的人工智能所异化。当然,这只是个人愿望。在人机共生时代,人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人类自身难以预料的。鉴于笔者对卡尔松范畴感知的自然审美模式持批判态度,范畴的缺失对于笔者主张的无范畴感知来说,不仅无碍,而且有益。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人类进化开始的时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能并未经过范畴的中介。通过范畴来理解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借用卡西尔的话来说,它是文化符号世界的产物。在未经范畴中介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关系,无论我们如何刻画这种关系,它都不是通过某个外在范畴来中介的,因此这种关系是无须习得的,是直接被给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关系,而非认知关系。借用杜夫海纳的术语来说,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前理解”状态。如果人类要理解世界就需要范畴的话,在“前理解”状态则不需要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处于“前理解”状态的人类对自然就一无所知,相反,人类可能有一种更接近事物本身的“元知”。杜夫海纳将在“前理解”中展开的世界称作“前真实”(pre-real)世界,一种比真实世界还要真实的世界,人在自然中最容易达到这种“前真实”的世界。杜夫海纳将“前真实”世界、自然与审美对象等同起来,他说:“审美对象的这种无用性和感性在审美对象中享有的优先性,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根本的外在性,一种自在的外在性,这种自在不是为我们存在而是将自身强加于我们,让我们除了感知别无依赖。在这方面,审美对象不同于使用对象而类似于自然对象。”“真正的对立在于自然物和人工物之间,丝毫不在于自然与艺术之间。”
自然的不可理解性,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中。诚然,我们可以用现有的艺术和审美范畴来理解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将它们理解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等,但是这只是我们人类的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在人机共生时代,人类很有可能不再需要从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之类的艺术作品中获得审美享受;人类可能会像这些艺术形式发明之前在自然中获得审美享受那样,去欣赏和评价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由此,人工智能艺术就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发现的,就像人类在自然中发现美那样,就像人类将某些现成品视为艺术一样。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类比:手工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源于作者在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源于对象在场,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源于观众在场。没有观众经验的激活,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作品将毫无意义。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不是从作品内部散发出来的,而是观众从外部赋予的。
人工智能艺术是观众发现的,就像自然美是人类发现的一样。但是,观众发现人工智能艺术的方式,不像科学家认知自然的方式那样。根据卡尔松的观点,科学家是通过为自然量体裁衣设置范畴来认识自然的,科学家教导我们通过他们设置的范畴来认识自然。但是,就像我们借助杜夫海纳现象学认识到的那样,在科学家能够为自然量体裁衣设置范畴之前,自然已经在他的“前理解”中呈现出来了。观众发现人工智能艺术的方式,就像自然在“前理解”中与人照面的方式那样,它们都是一种情感状态,而非认知活动。观众将令其感动的人工智能产品认同为艺术品,就像原始人将令其感动的自然物认同为美的一样。
正因为如此,在人机共生时代,作为观众的人类的审美能力和情感需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产品的理解不是从生产端而是从消费端进行的。不是生产什么就需要什么,而是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因为达到无限生产的生产力,可以生产任何东西,但人类并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们今天对人工智能艺术的理解,还是囿于从生产端的理解,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从消费端来理解。正因为如此,笔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的产品理解为自然,因为自然不是人类生产的,而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被发现的。我们可以设想人工智能艺术的3.0阶段,它无须人类提示词就可以生成无限量的产品。人类面对人工智能,就像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一样。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真正拥有了第二自然。作为第二自然的人工智能有不同于自然的地方:它只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有待人类的需要将它唤醒并变成现实。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艺术出现之前,人类艺术已经走到了它的极限,笔者将它称作处于临界状态的艺术。艺术不是终结了,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生了。也就是说,艺术不再是高级商品,而是生活方式。围绕艺术品的叙事终结了,接下来的是围绕艺术家的叙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生做成艺术,而不是将木头、石头等物做成艺术。如果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未来的艺术教育将不是以技巧为中心的专业教育,而是以审美为中心的美育。因为只有培养出人的审美需要,才能唤醒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艺术由潜能变成现实。
(文/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