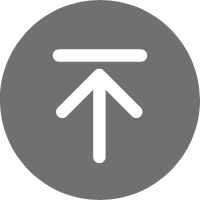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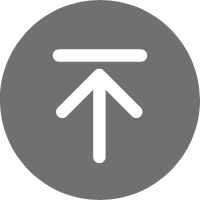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摘要:本文结合文献资料、现场测绘、图像分析和空间重构,对广胜寺下寺大殿壁画的原位问题及其观看机制展开讨论。文章指出,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写经图》(旧称《文殊伏案图》)应置于大殿南壁东侧的语境中加以理解;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藏《菩萨图》则应纳入大殿北壁东侧的佛会图体系。由此可见,这些壁画并非独立的图像单元,而是在特定的殿堂结构与宗教实践中生成了一个完整的观看秩序。本文就此为理解广胜寺下寺大殿壁画的整体视觉结构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广胜寺下寺 元代壁画 《写经图》 《菩萨图》 原位问题 观看机制
引言:图像为何必须“在场”
山西广胜寺壁画作为中国元代壁画艺术的高峰之一,因其保存完好的元代壁画体系长期受到中外学界关注。壁画不仅是宗教图像的承载体,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空间—仪式”系统,其原位性构成了其意义生成与观看机制的关键前提。近年来,随着壁画数字化与图册出版的普及,壁画图像逐渐脱离原有的建筑语境而当作“平面图像”孤立观看。无形之中,这一观看方式削弱了图像与空间之间的内在指向性,使其宗教性、仪轨性与实践功能消隐,壁画在当代的“再呈现”逐渐演变为一种脱离宗教与历史语境的视觉经验。
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通过对图像拼接、旧照光线与空间关系的综合分析,确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药师佛佛会图》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炽盛光佛佛会图》在广胜寺下寺大殿的原始位置,结束了此前关于广胜寺东西山墙壁画的争论,推动学界在其原位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此项考证使两铺壁画在文本语境、图像语境与空间语境中得以回归,大殿整体图像叙事与礼仪动线的结构关系得以被准确理解。〔1〕在多次实地勘察及与中外学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进一步注意到,尚有数幅此前未被系统论述的壁画,其内容与风格均与广胜寺下寺壁画存在密切关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图像原位的逐步厘清,其位置安排与视觉路径呈现出高度的空间规划性,并与已确立原位的两幅壁画之间形成明确的呼应关系。此一观察不仅补充了下寺后殿图像体系中长期缺失的部分,也再次表明:图像唯有回到其应在之处,其视觉呈现与宗教意义才能被完整而有效地激活。
一、壁画“在场”的图像学意义:空间不是背景
在传统佛教寺院建筑中,壁画从来不是被动的装饰性附属物,而是在特定建筑空间中承担具有“结构性”与“媒介性”的宗教图像。这些图像的意义生成,不仅依赖于其描绘的内容,更深深嵌入其所处的空间结构、观看路径与礼仪秩序之中。正如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所指出的,图像从未在真空中被观看,它“始终是在媒介之中发生的,而人的身体本身亦是一种活的媒介”〔2〕。换言之,图像的呈现方式与其材质、空间环境及观者的身体参与密不可分。一旦图像被从其原位抽离,它所依托的观看方式、文化语境乃至宗教功能便随之断裂。因此,佛教壁画的宗教意义不只是“被看见”,而是通过其在特定建筑空间中的位置、观看与礼仪实践,被不断“实践化”地激活。
近年来,关于佛教图像如何在观看过程中发挥这种“实践化的媒介性”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王慧兰(Michelle C.Wang)与林伟正(Wei-Cheng Lin)曾指出,佛教视觉文化的宗教效力并非源自图像所再现的叙事内容,而是通过观者的身体动作、行走路径与空间互动而生成。〔3〕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广胜寺下寺壁画的空间布局与观看方式,成为理解其图像如何在宗教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线索。下寺大殿中,壁画与造像的分布、尺度关系以及观者在殿内的移动路径,共同构成了图像的“实践环境”。图像不再作为孤立的叙事单元存在,而是在空间尺度、视线引导、图像组合与礼拜路径的协同作用下逐层展开,从而促成其“感通”“疗愈”与“护佑”等宗教效力的显现。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壁画“原位”的图像学意义,并以广胜寺下寺后殿图像的重新定位过程为切入点,旨在引发对图像与空间的互动如何成为意义生成的核心机制的再探讨,重思壁画图像的礼仪实践与观看机制,进而呼吁对其原位问题进行更加系统的再认知。
二、实证发现:广胜寺大殿壁画原位的再定位
广胜寺下寺大殿所构建的图像体系,展开于一座面阔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悬山顶的佛殿之中。〔4〕壁画在其中作为构成供养与礼拜系统的重要视觉媒介,通过与殿内造像、空间尺度、视线组织和仪式行为的互动,共同形塑出一套深具结构性的宗教视觉秩序。在此语境下,所谓图像的“在场”,并不仅指其存在于特定的壁面,而是指其通过构图、比例、人物动势等视觉策略,主动组织观者的身体移动与观看方式,并在礼仪实践与空间秩序中被不断激活。因此,任何脱离空间与仪式语境,仅依赖画幅主题内容或风格特征的判断,都可能导致误解。本文所展开的原位重构与空间重识,正是试图在“图像—空间—观看”三者交汇的层面上,恢复壁画在其原有建筑环境中的运作机制。
(一)关于《文殊伏案图》原位问题的再思考
有关广胜寺壁画的研究,层面之广、成果之丰,已不胜枚举。然而,既往成果多集中于题材诠释、风格归属、画工体系或宗教史脉络等方面,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相较之下,下寺大殿壁画的原位问题长期未得到系统梳理,而由原位变动所引发的图像意义、空间结构与观看方式的连锁变化,亦鲜少被纳入整体叙事框架中。事实上,一旦原位发生偏移,原有依托空间关系建立的叙事逻辑便随之松动,相关研究所赖以成立的空间前提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动摇。
在此背景下,现藏于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的《文殊伏案图》 (图1)尤具关键意义。该作的图像主题、人物身份与原属地问题长期存有争议。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埃伦·B. 阿夫里尔(Ellen B. Avrill)尝试从图像叙事入手,将此图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所藏《炽盛光佛佛会图》联系,认为画中主角可能为“受炽盛光佛启示的文殊菩萨”〔5〕。然而,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宾大壁画已被确认并非出自广胜寺,其所提出的图像对应体系随即失去基础,人物身份再次陷入模糊。

图1《文殊伏案图》壁画 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 图像来源/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CAEA)数字库
追溯更早的史料,则可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1935年,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明确记载:下寺后殿南壁曾绘“无著、天亲二大士”〔6〕。与之相互呼应的是,周肇祥(无畏居士)亦于《艺林月刊》第47期(1933年11月) 《广胜寺发见北宋錾经卷纪略》一文中提到“下寺画壁甚古,有无著、天亲二菩萨象一堵,数年前为厂估购取……”〔7〕。就目前所能检索的史料来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史料传递关系,为此图与无著—天亲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的早期线索。近年来,左奇志通过梳理流传路径、题记信息、壁面尺寸,以及广胜寺近现代维修史,提出一套关于《文殊伏案图》原位的新框架,并推测其或可视为《世亲写经图》。左文在排除法与空间逻辑方面具有启发性,然而,在关键证据的论证路径与证据层级处理上,其方案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空间。〔8〕为行文便利,下文暂以“《写经图》”指称之。
笔者以为,关于《写经图》的图像内容与原位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争议,一方面源于壁画早已脱离原有墙体、失去与建筑空间的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亦因现存材料中图像语义与观看方式的模糊。为此,本文试图从目前发现的新材料入手,将图像自身的视觉线索与殿内空间结构重新联系起来,以期在原位与图像内容的辨析上取得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在左文既有成果之上,就具体的原位推断方法与证据的使用方式再作进一步讨论,以期对相关论证予以补充和细化,重新思考《写经图》在广胜寺下寺大殿图像体系中的空间位置及其意义。
其一,关于以现状尺寸推断原位的问题。左文首先依据北壁空白处的宽度约286厘米与《写经图》现宽297.3厘米之间的差距,否定其原位于北壁的可能;继而测得南壁西侧宽290厘米、东侧宽297厘米,并据此指出南东壁在数值上“差距几可忽略不计”的接近程度。然而,当题记被他释为“南西壁”,而南西壁宽度较画幅窄7.2厘米时,论证逻辑随即转向,以《重修广胜下寺佛庙序》碑文中“重修庙内大殿三处”“壁面需重新修葺粉刷”为据,认为墙体在近代重修中“出现几厘米的偏差当有可能”。换言之,在排除北壁等其他壁面时,作者事实上默认“现状即原状”;而在南西壁尺寸明显不足时,则引入“墙体尺度可变”的前提,以消解这一不利因素。这一逻辑前后并不一致,加之后殿墙体与画幅自身均可能因修复产生尺度误差,使基于尺寸比对的判断存有局限。
其二,关于题记首行“南壁”释读问题。左文在指出题记首行“南壁”漫漶不清之后,先排除“南周壁”“南尹壁”等地名的可能,继而以广胜寺水神庙题记中“西壁”字形为参照,认定漫漶处“与‘西’字十分吻合”,遂将该行断为“南西壁”,并据此视为确认原位的关键信息。此判断虽具可能性,然在字迹保存状况不佳、可供比对的字形样本较为有限的前提下,直接据此排除与其字形结构同样接近的其他可能(如“两”字),仍显证据不足。依笔者对残存字迹的观察,该字并非必然为独体字,亦不排除其具有左右结构的可能(如“拐”字),相关释读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左文以“尺寸吻合南西壁”与“题记可读作南西壁”相互印证,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原位假设,但若要将之提升为排他性的定论,仍缺乏来自建筑史、修复史、题记学、旧影像材料等多方面的交叉证据。在现阶段,更为稳妥的方法或在于:将“南西壁”视为若干可能原位之一,并与后殿整体图像程序、对称结构与礼仪动线的综合考察结合起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写经图》原位问题并非简单的“图像归位”,而牵连着对广胜寺下寺后殿整体图像程序的“空间重识”与宗教实践形态的重新理解。
1. 旧照的回溯与再激活
正因上述证据体系尚未稳固,关于《写经图》原位的进一步讨论需要跳脱仅依赖现状尺寸与残字释读的路径,重新回到壁画未脱壁前的历史现场。值得注意的是,广胜寺的早期影像材料并非近年来才被整理出来,而是早在201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研究员陆聆恩在其《元代广胜寺下寺壁画的颜料风格与作坊实践》 (Pigment Style and Workshop Practice in the Yuan Dynasty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Lower Guangsheng Monastery) 一文中,即已首次引用了《艺林月刊》所刊载的20世纪30年代旧照,并将其中两帧影像分别认定为“文殊”与“普贤”菩萨(图2、图3)。〔9〕然而,这些旧照在陆文中仅作为图版引用,其图像内容考订及其所涉及的空间关系以及可能的原位线索,并未进一步讨论。

图2 赵城广胜寺画壁二 《艺林月刊》第50期

图3 赵城广胜寺画壁 《艺林月刊》第49期
因此,本文再次回溯这批旧照,对《艺林月刊》47期至53期中的数帧影像与相关记述重新进行比对、释读与空间分析,试图让这些被引用却未真正进入原位论证体系的材料重新发声。更重要的是,这批旧照所呈现的原始信息使我们得以更贴近壁画原有的空间语境,也为重新评估《写经图》的原位提供了新的视觉证据链。基于上述史料与视觉材料的重新整理,本文将结合《艺林月刊》旧照与广胜寺下寺后殿的空间格局,重新展开对《写经图》原位的空间重识。
在回溯这批旧照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艺林月刊》第50期刊载的一帧题为“赵城广胜寺画壁二”的旧影(图2),实为《写经图》尚在原壁时的影像记录,然其旁未附相关说明。而《艺林月刊》第49期中一帧题为“赵城广胜寺画壁”的旧照(图3)则附注:“无著天亲二菩萨象、已为人盗宝、此其一焉、画法遒古、定出唐人之笔也。”除这短短数语之外,刊物并未提供更多信息。除陆文外,过去学界多将《写经图》作为孤立的单幅图像讨论,因而其意义被限定在单张画面的内部结构之中;随着图3等新材料的出现与并置,这些旧影像被重新激活,其原本作为“单幅”的视觉单元可能转化为一组画面的片段,其图像的感知方式、理解框架与使用逻辑随之发生变化。这也为重新审视《写经图》原位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图像、构图与成组性判断
当图像从“单幅”转化为“组画片段”之可能性被提出后,其内部的视觉组织方式亦需重新审视,因此,可以通过画面细节探讨其图像内容与构图回应这一新的理解框架的可能性。
《写经图》中,菩萨端坐宝座之上,凝视案前素卷,身微俯,手执笔;左足轻抬,与欲书未落的右手形成呼应,显现出凝神沉思、意在书写的动态瞬间。几案之上,文房器具陈设井然,自左下至右上依稀可辨砚滴、砚台、墨锭、镇纸、压尺与笔屏。案侧一朱颜梵像侍者手捧卷轴,神情恭谨,似静候随侍。画面右上尚存墨书题记,笔者尝试辨识:“南壁绘,望日乡上张村……王思斋、李享、李通、小贵法师、高祐德、各保自身,愿门傯速静,长幼咸安孝,至正十四年岁次甲午季秋月毕。”部分文字漫漶,但从内容结构判断,此当为供养题记,主要记录施主姓名及祈愿事项,非画工署款(图4)。

图4《写经图》题记 图像来源/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CAEA)数字库
相较而言,图3尽管影像模糊,仍可辨认菩萨右手挽袖、左手抚已展开至中段的经卷、俯身伏案,双目低垂凝视案前铺展的经文,呈现一种凝神体悟、若有所思的状态。其动态与《写经图》中的人物高度对应,而书案与宝座亦随人物动态呈对角斜向布置。尤须注意的是,《写经图》中自画面左下至右上的人物与书案排列,与图3中的人物与书案共同形成斜向组织的构图模式。在本案中,这种自一隅斜向展开的构图方式,并非单纯的形式处理,而似是画师在墙面上主动制造空间推进的尝试:观者的视线由人物转向书案,再被引向画面外部的隐藏空间,使画面呈现出超越壁面的延展性,营造出一种几欲令人步入的错觉式纵深体验。
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一对角线式构图不仅强化了画面内部的空间深度,也含蓄地预设了其与殿堂建筑空间的呼应关系。换言之,两图并非孤立成画,而是以左右相对或相背的方式置于壁面之上,使二者形成成组呈现、彼此补充的视觉装置。此种对置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互证性:倘若其中一幅的原位能够加以确认,则另一幅亦可据此归位,从而在佚失与残损之间重建更为接近历史现场的空间叙事。因此,如何从画面有限的视觉线索中探寻其在殿内的方位,便成为原位考证的关键一步。
3.《写经图》原位的空间推断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下寺大殿南壁两侧的基本尺度。经笔者实地测量:南壁东侧墙基高约90厘米,墙基之上窗东侧墙面高约430厘米、宽约305厘米;南壁西侧墙基亦高约90厘米,墙基之上窗西侧墙面高约440厘米、宽约290厘米(图5)。需要说明的是,大殿曾经历“墙顷像毁”之险,后期修复后的墙面亦非全然平直,故文中所用尺寸均取实测中的最小值,以避免因墙体变形而造成推断偏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墙面可供绘制的宽度与长度,与辛辛那提《写经图》高416.8厘米、宽297.3厘米的尺幅高度契合。上述数据不仅为其原位推断提供了重要的尺寸依据,也为后续的空间推断奠定了必要的建筑尺度基础。

图5 山西广胜寺下寺大殿南壁尺寸示意图
在相关资料的检索过程中,笔者注意到陆文中引用了一帧拍摄于1934年的旧影(图6)。〔10〕画面呈现广胜寺下寺大殿内数尊罗汉造像,形态各异,坐于龛中。结合大殿仅南壁开窗的建筑特征,可依据光照方向推知该影像的拍摄位置应在西山墙一侧。无独有偶,《艺林月刊》第48期亦刊载一帧广胜寺罗汉旧影(图7),题为“赵城兴善寺古塑罗汉象”,旁注“奇古生动、几欲抗衡杨惠之、定出宋元名手也”。经比对可知,该图所示造像正为前述旧影中居中的一尊,而题中“兴善寺”显系“广胜寺”之误。上述影像材料与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所记“东西山墙下十八罗汉,并无特长,当非原物”之语亦可互相印证〔11〕,从而为追索下寺大殿内部造像的历史位置及其与壁画之间的空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6 1934年广胜寺下寺大殿西山墙 图片来源/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档案

图7 赵城兴善寺古塑罗汉象 《艺林月刊》第48期
基于上述材料,本文从两条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印证的路径,对《写经图》的原位问题加以讨论。
其一,以图2所示旧照为分析起点。图2画面左下方可见一件上窄下宽的异形物体,其后方清晰显露出一处木质构件。由于该构件与壁画画面直接相接,二者在垂直方向上必然存在明确的标高对应关系。通过将图2与馆藏《写经图》现状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旧照中壁画右上角题记顶部、人物头光中火焰纹的最高点与墙体顶部几乎重合。结合现存《写经图》的保存状况,可知画面上部基本未见明显缺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图2中该木质构件与画面中宝座扶手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反推其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以《写经图》现状测量数据为参照,宝座扶手距画面顶部约220厘米;再结合南壁两侧现存墙体高度在墙基之上为430—440厘米,可推算该木质构件距墙基之上的高度应约为210—220厘米。该高度与西山墙神龛龛楣的实际标高基本一致(图8),因而可以合理判断,图2中所见木质构件应为神龛的龛楣部分(图9)。

图8 广胜寺下寺大殿西山墙标高关系

图9 木质构件标高推算示意图
在此基础上,将图2与笔者实地拍摄的南壁东侧现状照片加以对照,可以进一步发现:旧照中窗侧墙面、龛楣及前置构件均受到来自画面右侧的自然光照亮。该光照方向并非偶然,而是由大殿采光格局所决定。大殿仅南侧开窗,且南壁两段可供绘制的墙面分别位于次梢间窗的两侧,因此,靠近窗的一侧会形成更强的侧向入射光。就图2而言,亮部集中于画面右侧,结合建筑方位可知,画面右侧对应西向。正是在这一建筑条件下,旧照中所呈现的光照方向才得以形成。由此可知,图2中所呈现的受光状态是由南壁东侧特有的“窗—墙”空间关系所决定。与此同时,旧照与现状照片在墙面转折等建筑结构细节上,亦能够实现合理对应(图10)。综合前述标高推算、自然光照规律与建筑结构细节三重证据,可以判断,图2所示《写经图》原应绘制于大殿南壁东侧。

图10 广胜寺下寺大殿南壁东侧现状与旧照建筑结构比对 制图/韩茂远
其二,以图3为对象展开推演。图3右下角残留一处白色光斑,其形状呈椭圆,边缘相对清晰,具有明显的受光反射特征。其与图6中左侧罗汉头部在光照条件下所呈现的反射特征较为接近。同时,其在旧照中所呈现与壁画的空间关系,亦与前述以龛楣标高为参照所推断的罗汉造像与壁画之间的空间关系大体一致。综合光斑的轮廓形态、受光方式及其与壁画的相对位置等因素,将其解释为一尊罗汉造像头部的受光反射,较其他解释更为合理。若此判断成立,则图3所示壁画应位于一尊罗汉造像相邻的壁面之上。进一步结合图2中壁画与龛楣紧密相接的空间关系,以及图6所示西山墙南侧龛楣已缺失的现状,可以解释图3中未见龛楣构件的原因。考虑到罗汉造像通常面向殿内布置的陈设惯例,而与其相邻的壁画亦随之形成对应的空间关系,由此可推知,图3所对应的位置为大殿南壁西侧最为合理。
以上两条路径分别从木质构件与壁画的标高关系、殿内采光规律与建筑结构细节,以及造像与壁画的空间对应关系展开推演。尽管所依据的材料类型不同,但所得结论高度一致:图2与图3原应分别设置于下寺大殿南壁两端,构成一组相互呼应的成组壁画。结合现场测量数据可知,两幅壁画在构图、比例与所需壁面尺度等方面,均与南壁空间条件相吻合。影像材料、图像逻辑、空间关系与建筑尺度由此形成一条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若进一步参照佛教空间中常见的“左尊右卑”陈设原则,以及周肇祥、蒋唯心关于“无著—天亲”兄弟的早期记述,再结合前文对两图原位的空间分析,则可以提出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推测: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文殊伏案图》或为《无著写经图》,图3则可能为《天亲写经图》。笔者在上述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为呈现两幅壁画在实际建筑环境中的视觉关系,进一步对其在大殿空间中的原位效果进行了复原模拟(图11)。

图11 广胜寺下寺大殿南壁复原示意图 制图/韩茂远
(二)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菩萨图》原位问题的再思考
在厘清《写经图》与下寺后殿南壁的原位关系后,本文将视线转向另一幅长期脱离原境的重要遗存——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藏《菩萨图》(图12)。该作因脱壁年代久远,长期缺乏关于其原位的系统讨论。然而,其图像结构、画面风格与人物造型特征,均提示其有与元代晋南壁画体系进行比对的必要性。对该作的图像属性与可能的空间指向进行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澄清其自身的图像学特征,也为探讨其潜在的原位提供重要方法论基础。基于此,本节将首先从图像与风格层面对其进行分析,继而回顾既有研究的侧重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晋南地区相关图像材料进行比对,以探讨其原位问题的可能性与合理范围。

图12 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藏《菩萨图》
1. 作品形制与流传脉络
现藏于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菩萨图》(DIA馆藏号51.1)为一幅自寺院壁面脱离后,经重新配板与补绘而成的壁画残存。据馆方资料显示,该壁画绘制于14世纪至15世纪,现存尺寸为334×178.4厘米,于1951年由卢芹斋(C. T. Loo)捐赠入馆。画面显示该作现由三块木板支撑并拼接而成,共嵌入十六片原壁残块:最上方木板仅嵌有一片原迹,正为菩萨头部,惜中间断裂,其余部分皆以补绘填充;其余十五片残块则分别按顺序拼置于下方两块木板之上。各残块边缘均呈不规则断裂状,显露出脱壁后再行组装的明显痕迹(图13)。

图13《菩萨图》分割情况 制图/韩茂远
在流传脉络方面,该作最早见于卢芹斋1941年刊行的《中国艺术品图录》(图14),彼时被断为“宋代”。值得注意的是,图录所附影像显示该作保存状态较今日更为完整:最上方木板左上角仍可辨部分衣纹与璎珞的局部细节,而这些部分现已不存。图录同时注明,此次展览为“特展”(Special Sale),展期为1941年11月1日至1942年4月30日,地点位于卢芹斋纽约画廊——麦迪逊大道595号东57街41号。卢芹斋在序言中特别指出,展览销售收入的3%将用于中国抗战时期孤儿救济。在他的表述中,购买者不仅能够“购得心仪之物”,亦能在“支持伟大事业”的意义上参与对战争孤儿的援助。〔12〕这些信息不仅构成作品流通史的重要背景,也反映了卢芹斋在战时艺术品经营与慈善募款之间的复杂策略。此外,1950年摄影师妮娜·雷恩(Nina Leen)在为LIFE杂志拍摄卢芹斋位于其画廊的报道照中,亦清晰记录下该作悬挂于其展厅墙面的陈列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画面左上角的衣纹与璎珞已不复可见,其保存状况与现状较为接近(图15)。〔13〕该影像不仅揭示了作品在流散过程中的实际陈列状态,也为追踪其脱壁后的流传路径提供了直接的视觉证据。翌年(1951),该作由卢芹斋捐赠入藏底特律艺术博物馆,完成其目前可考的流传路径。

图14 1941年卢芹斋《中国艺术品图录》中的《菩萨图》 大观堂文物文献博物馆提供

图15 卢芹斋在《菩萨图》前留影(Nina Leen, “C. T. Loo & Co. Liquidate”s, 1950, LIFE Photo Collection)
2. 研究现状与既有判断
目前可查的公开资料中,DIA数据库(Published References)项为空,显示该作至今未进入既有学术体系,也未见专文对其来源、风格或原位展开系统讨论。其年代、归属皆处于资料空缺状态,使其既成为研究中国壁画流散现象的重要案例,同时也为展开原位考证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从宏观脉络看,该作出现的时间与卢芹斋在20世纪30—50年代大量收购、转移北方寺院壁画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然而,尚无直接文献可证其源自何处,亦未有证据显示其与某一特定寺院存在必然联系。正因如此,对该作的讨论必须回到图像本体,并结合风格、构图与空间证据进行逐层比对,而不可先入为主地进行归属判断。
在既有研究中,相关的原位推测仅呈零散式出现。2019年,瞿炼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该作可能原属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东侧,但其论述仅止于方向性提示,并未展开进一步论证。〔14〕2023年,孟嗣徽根据图中人物坐姿、风格特征及尺寸比例与兴化寺后殿壁画的相近性,提出其或为该殿另一山墙上主尊佛的右胁侍菩萨。〔15〕综合上述研究可见,相关讨论虽已涉及不同可能性,但尚未形成可供广泛接受的明确结论。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系统的图像比对与空间关系分析,对这幅流散壁画的可能原位进行更为严密的考察,以期在现有证据框架内提出一个相对稳健、可供检验的推论。
3. 图像结构与风格分析
尽管《菩萨图》经历分割、揭取与再装裱,其现存残块仍保留足以支持图像学分析的关键视觉信息。画面为一尊正向而坐的菩萨像,其左足盘起,右足自然下垂,踏于盛开的莲花之上。菩萨高髻饰花冠,眉目细长,鼻梁挺直,面容呈椭圆形,轮廓柔和内敛;胸前璎珞结构繁复,由连珠、复瓣与垂饰组合形成递次下垂的节奏;衣纹描绘兼具挺劲与柔韧,宽边天衣虽有残损,仍可辨识团花纹样。菩萨右手掌心向上做轻托状,左手微向画面左下伸展;细致的腕指动作,使正面而坐的姿态在稳定中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须弥座的刻画尤为精致,其上部细密缠枝牡丹,下层饰戏珠龙纹,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显示其在佛坛体系中应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画面最下缘还可见一处圆光上部残迹,其中可见火焰纹,暗示原画下部可能包含供具或焚香等情境元素。
画面右侧尚存一半身人物,宽袍大袖,虽面部已佚,但头光仍清晰可辨,其服饰形制表明其身份应为男性侍者。其身后一位双髻侍女侧身探出,双手托盘,盘中所绘珍宝尚可辨识珊瑚、摩尼宝及牙角类器物。与常见随侍形象不同,该侍女并未面向主尊,而是侧首向画外方向注视。此种处理打破了人物与主尊之间的单一从属关系,将其从原有的图像框架中“解放”出来,与殿内的观者形成直接的目光接触。使图像构成一种超越壁面平面的叙事张力:其不再是封闭的视觉单元,而是主动与殿内空间互动的“观看装置”。
在完成上述图像结构分析后,再观其设色。画面以石绿、石青等冷色为主调,局部辅以赭黄、朱砂等补色点染。莲花、肤色及天衣以白、肉色等亮色过渡,使画面在厚重与清润之间形成富有层次的色彩节奏,符合晋南地区壁画惯见的赋色模式。线描手法上,画中以“铁线描”的劲挺为主,间以“兰叶描”表现衣纹的舒缓,而最具辨识度的,是线条之间清晰的组织与避让关系:线与线在交接处以微弱的间离、退让处理,既避免线条堆叠的混乱,也通过“空隙”与“让位”自然区分物像的主次与前后的空间关系。“以避让造空间”的线描手法,正是晋南地区元代壁画所共同呈现的区域性笔法传统,其功能既为塑造体积感,也在平面中建立清晰的视觉秩序。尽管本幅壁画部分区域经后世补绘,但在原迹保留部分中,这一线描体系的结构逻辑依然清晰可辨,为探讨其风格归属与原位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依据。
综上所述,从人物造型的比例与姿态、冠饰及衣纹的组织方式,到设色体系的层次处理,再到线描所呈现的劲挺特征及以“线条避让”塑造主次与空间的区域性线描风格,《菩萨图》在图像结构、设色与线描手法上均与晋南地区元代壁画的整体风格谱系相吻合。其风格母本应在广胜寺、兴化寺、青龙寺、永乐宫等同一地域文化圈的壁画系统中寻求理解。正因如此,对其原位与归属的进一步探讨,必须置于晋南地区壁画整体风格与空间结构的框架下展开,方可获得更为可靠的判断基础。
4. 图像比对与原位推测
在确认《菩萨图》于人物造型、线描手法与设色方法上均可纳入晋南地区元代壁画传统之后,下一步的关键问题即在于:如何在这一较大的区域风格框架内,进一步限定其具体出处与原位。基于此,本节从图像尺寸、画面内容、壁面空间组织等角度,依次将《菩萨图》与晋南地区相关壁画材料进行比对,从而探讨其原位的可能性。
在图像可比性方面,经笔者检索,当下仅有三组材料可为《菩萨图》提供直接的图像参照:其一,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兴化寺《弥勒说法图》;其二,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所藏《药师佛佛会图》;其三,现存于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的局部壁画(图16)。

图16 左: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弥勒说法图》(局部)
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局部)
右: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壁画遗存
首先,从人物动态观察,《菩萨图》中的人物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弥勒说法图》右胁侍菩萨在坐姿、动态与衣纹披垂方式上呈现高度相似性,提示二者之间可能有粉本上的传承或借用。然而,兴化寺已于20世纪初毁于战火,其原有殿堂结构与壁面布局已不可复原,使得进一步探讨在现阶段难以展开。其次,《菩萨图》中颇具辨识度的宽边天衣处理手法,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中左胁侍菩萨所见衣饰较为接近,显示出某种图像母题上的关联性。但两者之间亦存在显著差异: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壁画中的菩萨略呈侧身面向中央主尊,而底特律本则为正面而坐。随着近年研究的推进,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本已基本确认并非出自广胜寺,因此,其图像特征难以被用作《菩萨图》原位的直接判断依据。综上,在可比图像与可用证据的局限下,笔者将视线转向第三组材料——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的残存图像。
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现存壁面规模约为480×2650厘米。壁面东侧尚可辨识一佛、一菩萨与一护法,余部多已漫漶,整体信息极为有限。然而,东西两端壁面均可见明显的切割断缘,其西侧切割尺寸约为480×270厘米,东侧切割尺寸约为380×210厘米,均略大于底特律本《菩萨图》的整体尺寸(334×178.4厘米)。此一点提示北壁同样曾遭遇较大规模的揭取或破坏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北壁东侧残存的菩萨虽因漫漶严重已难辨五官细节,但其大体坐姿仍依稀可辨:菩萨正向而坐、其右足盘起,左足下垂踏于莲花之上,且从残迹亦可见其随动态自然下垂的宽边天衣。此种宽边天衣的处理方式,与《菩萨图》中所见的菩萨衣饰特征高度一致,这在晋南元代菩萨造型中并非普遍现象(图17)。基于上述图像信息,笔者尝试将《菩萨图》与北壁东侧残迹进行数字化拼合。拼合结果显示,无论从主尊与胁侍的相对位置、两菩萨的镜像构成关系,还是从《菩萨图》右下角侍者与北壁东侧残存人物的对应关系来看,均呈现出一种高度吻合的状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菩萨图》左上角残存的人物边缘与北壁东侧上方残迹在衣纹走势亦能够形成较为自然的衔接(图18)。这一对应关系提示,1941年图录中该部位所呈现的较为完整的衣纹与璎珞细节,未必反映原始画面状态,而更可能为卢芹斋所作的修补性添绘。结合1950年卢芹斋画廊照片可见,该部位衣纹已不复存在,显示相关添绘应在作品进入博物馆收藏之前被去除,由此造成图录影像与现状之间的差异。

图17 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壁画遗存与《菩萨图》

图18 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壁画虚拟复原 制图/韩茂远
总体而言,尽管北壁现存信息较为有限,但综合切割断缘尺寸、残迹形态特征与数字拼合的可行性等多方面证据,可以较为明确地判断:现藏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菩萨图》应出自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东侧,其所绘菩萨形象当为东侧佛会图中的左胁侍菩萨。进一步结合广胜寺下寺大殿震后维修的历史背景及该作在造型处理与图像风格上的特征判断,此幅壁画的绘制年代应与大殿东西山墙壁画相近,约可定于14世纪早期。
三、归位后的观看机制与空间重识
在前文分别完成《写经图》与《菩萨图》的原位推断后,有必要将这些图像重新置回广胜寺下寺大殿的整体空间之中加以审视。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些壁画并非孤立存在的单件作品,而是围绕佛坛并依托殿内实际观看路径,形成彼此呼应、具有明确空间指向的整体叙事结构。在这一整体框架下,壁画原位的意义已不止于确定单幅图像在墙面上的位置,而是直接关系到大殿内部观看路径的生成方式。壁画在此既承担供养与仪式的宗教功能,同时亦通过其空间位置与图像指向,主动介入观者的行走、驻足与观看过程。原位的重新确立,因而为理解后殿壁画所营造的观看机制与空间叙事提供了关键前提与稳固框架。
(一)《写经图》观看的可能性
广胜寺下寺大殿的空间结构,使南壁壁画在殿内诸壁之中呈现出独特的观看属性。与东西山墙两铺佛会图中主尊正面而坐、承担“供人参仰”主要视觉功能的格局不同,南壁两侧《写经图》中的菩萨皆作侧身伏案之姿,其朝向与动势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视觉引导性。由于殿内仅南壁设窗,使其长年处于逆光或侧逆光状态,加之后殿采用“减柱”“移柱”并后移佛坛,使殿内具备了可供仪式活动与集体观看的宽阔中央空间。〔16〕在这一特定的建筑语境中,《写经图》的观看并不遵循一般壁画以“迎视”为核心的观看模式,而是在光线、空间动线与宗教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重层次、具有时间性的动态观看。为了清晰呈现这一视觉体系,以下将从四个相互关联的观看机制加以讨论。
1. 窗·图像:在时间中观看
根据笔者实地测量与现场观察,若将《写经图》的尺幅与南壁的实际高度、宽度相互对照,并将其置于南壁窗侧位置,则画面与建筑之间形成一种高度契合的“嵌合关系”。壁画中案几的高度、人物伏案书写的姿态,与南壁东侧直棂窗的高度恰构成视觉上的对位,使观者在观看时自然将“窗—案—人”视为一个复合性的图像场域。更为关键的是:窗洞引入的自然光并非图像之外的条件,而是被吸纳进壁画的叙事结构之中。光线方向与人物伏案书写的动势一致,使画中书写行为与现实光源建立了空间关联。由此,《写经图》不再呈现封闭的室内场景,而是构成一幅“窗下写经”的开放性图像:窗外的四季变换、日出日落的时间节律均可能在观者的观看经验中“进入画面”,使静态壁画在实际观看中呈现随时间展开的景观性。
这种“现实景物—图像情境—时间流动”的三重互动机制产生了近似装置化的效果,使观看行为本身被纳入图像结构之中。从这一前提可知,《写经图》原位于南壁窗侧不仅在尺寸上可行,更在观看逻辑上具有高度合理性。
2. “讲经”与“回望”:宗教行为中的观看路径
在上述视觉前提下,《写经图》的观看进一步与宗教行为发生关联。当观者步入大殿时,其第一视觉焦点多落于佛坛之上的造像与两侧的佛会图,南壁则因背光而并非初始主视觉。然而正是这一观看延迟,使南壁壁画在宗教仪式中承担回望的功能。从空间动线推测,主持僧人在殿堂中央讲经时,面对的正是南壁东西两侧《写经图》。两图中案几皆呈斜向展开,在空间中形成自然围合,其指向性恰落于殿堂中央的讲经区域。图像中伏案菩萨的目光亦非完全落于案前经卷,而略向画外延伸,看向站立于中央的讲经者或信众位置。由此,观者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被纳入视觉叙事之中,成为完成整个观看机制的关键环节。换言之,观者以缺席的方式被永远预设在这一位置上。《写经图》中斜置的桌案与俯身前倾的人物显著强化了画面的纵深效果,在壁画与观者之间制造出一种无形的张力;这种构成通过姿态与方向性的迎合,引导观者产生向画面靠近的观看趋向,并被纳入图像所营构的空间之中(图19)。当观者完成参仰或听经后转身欲出殿时,南壁成为其视线所抵达的最后图像区域,形成“入殿观佛—出殿见经”的视觉闭环,使《写经图》在宗教实践层面形成一种明确的观礼终点。

图19 广胜寺下寺大殿南壁东侧壁画观看示意图 制图/韩茂远
3. 主尊的“注视”:佛—观者—图像的三重视域
在“入殿观佛—出殿见经”的观看路径中,南壁《写经图》并非仅作为观礼结束时的被动图像而存在,其空间意义还可进一步深化。归位之后,两幅《写经图》所围合出的空间视域,恰与殿中佛坛上毗卢遮那佛的注视视域相重合(图20)。由此,南壁两幅书写经文的菩萨、殿堂中央的观者以及佛坛之上的主尊佛,共同构成一个主尊佛—写经菩萨—观者相互关联的空间叙事系统。

图20 佛—观者—图像的三重视域 制图/韩茂远
在这一系统中,菩萨以书写的姿态向佛与观者展呈经文,观者立于二者之间,成为激活图像与空间的必要一环。而毗卢遮那佛居于殿中正位,将两幅《写经图》纳入其注视领域。因此,南壁的图像不仅描绘写经行为本身,更构建出一个由佛陀观看、由观者参与的神圣场景。《写经图》因而并非孤立的壁画,而是整个大殿视觉、仪式与空间结构的关键组成。其意义正在于通过书写之仪,引导观者进入佛的法界秩序之中,构成“讲经—观想—礼佛”相互贯通的观看机制。
4. 法界的“外延”:图像向殿外空间的指向
若结合图像构成与大殿空间加以考察,两幅《写经图》在归位后呈现出一种具有指向性的视觉策略。两幅画面中的宝座、桌案、铺陈的经卷及人物动势,均沿对角方向指向南方,其视觉消失点自然延伸至殿门之外。由此使大殿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在视觉上产生连通,形成一个开放而流动的视觉场域。这一构图方式意在突破壁面的物理限制,使南壁不再成为观看的终点,而更接近于一种“通景画”式的界面。从而,《写经图》组画的视觉组织并未将叙事限定于殿内,而是主动将观者视线引向殿外,使南壁在空间与宗教意义上同时具备双重属性——既是殿内法界叙事的终点,也是向殿外延展的起点。从建筑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处于内外空间交汇处的区域,恰可对应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所提出的“阈限”(liminal)概念,即介于两个状态之间、具备转化性和开放性的过渡区。〔17〕在此类区域中,空间转换、视觉引导与行为仪式往往被同时激活,《写经图》正是在这一位置上,将观者的观看由殿内法界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从《菩萨图》出发:北壁叙事体系重建的可能
在前文对南壁《写经图》观看机制加以厘清之后,下寺后殿的视觉结构已显露出一种由空间组织、图像引导、观者参与而得以激活的多层次体系。然而,这一观看机制并非仅由南壁单向构成。作为殿内另一重要壁面,北壁同样参与了整体视觉与宗教叙事的组织。相较于南壁图像对观者行走与观看的引导功能,北壁位于大殿的正面区域,更可能承担正向观瞻、佛会展开的视觉秩序的职能。因此,在确定南壁观看逻辑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北壁的空间布局与残留图像,进而探讨其在后殿整体观看体系中的角色与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北壁的画面结构呈现出与既往认识明显不同的形态:其并非由单幅佛会图构成,而是由分布于东西两侧的两幅大型佛会图组成。两幅壁画均为“一佛二菩萨”样式,高约480厘米,通长约1100厘米,构图形制与东西山墙壁画相近。北壁当心间原设有一门,门上方红框内绘有人物数身,今因漫漶严重而难以辨识。该门原为殿内通向后院的通道,至明代被封堵,其上补绘有云气纹样,以实现与两侧佛会图之间的视觉过渡与衔接。〔18〕经此处理,原本功能性的门道转化为壁面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今日可见的完整北壁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一帧来自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34年的旧照显示,佛坛之上曾设有一大型佛龛〔19〕 (图21),据文献记载,此龛应为1622年广胜寺众僧“募十方信众”所“加增焰光”之作。〔20〕照片中可见佛坛上主尊毗卢遮那佛及其胁侍菩萨,龛楣题“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字样。此龛规模宏大,使其北侧壁画在当时已被完全遮蔽,原本面向殿内的图像遂退居为造像“背景的背景”。这一变化是否意味着在明代增建佛龛之后,北壁壁画的功能由可供观看的图像转向更具象征性的参仰,尚有待进一步讨论。然而,这一历史事实至少表明:该大殿空间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与重构,其图像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多元且动态演变的叙事结构。因此,对其图像意义的理解,也必须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

图21 1934年广胜寺下寺大殿毗卢遮那佛塑像 图片来源/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档案
鉴于现存材料的局限,本文并不尝试对北壁的叙事体系进行重建,而将重点放在确立北壁“双幅佛会图”这一基础性空间发现上,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坚实的结构框架,也为学界进一步关于北壁图像体系的研究打开空间。
结 语
通过对旧影像、现场尺度、构图语言与空间结构的交叉分析,本文确立了《写经图》组画原应分置于广胜寺下寺大殿南壁东西两侧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指出,现藏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菩萨图》与大殿北壁东侧佛会图在构图规律与图像要素上具有可验证的内在对应关系,从而明确其原属该壁面体系。
三幅流散与残存图像在完成原位重建之后,不再作为孤立的视觉片段被理解,而被重新纳入同一殿堂空间中,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秩序的整体视觉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图像的意义被重新置回其生成机制之中。相较于近现代以来壁画通过画册复制、数字化展示及博物馆陈列等方式不断被“再语境化”,并被观看为可脱离原有尺度与建筑位置的独立图像单元,原位重建使其重新回到作为殿堂建筑组成部分的空间语境之中。壁画不再以类似架上绘画的方式被孤立观看,而是通过其具体的空间位置、与观者行走与观看路径的关系,以及与宗教仪式实践的结合而被激活,重新成为构造宗教经验的实践性媒介。这一重建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因图像脱离建筑语境所造成的视域偏差,更揭示了广胜寺下寺后殿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出的多重叙事结构。图像的原位因此并非考古意义上的“坐标恢复”,而是一种对视觉路径、宗教功能与空间秩序的整体重识。
由此可见,唯有将壁画置回其应在之处,其所承载的观看机制、宗教效力与空间意义方能正确激活。原位重建不仅让观者得以更为精确地把握广胜寺下寺大殿的图像系统,也提示我们:壁画艺术的意义从来并非封闭于画幅自身,而是在建筑空间、仪式实践、观者身体与时间流动的持续交互之中不断生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广胜寺下寺后殿壁画为我们重新思考壁画艺术与空间、观看及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案例。[致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研究临摹”项目得到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全力支持与资源共享,以及何慕文先生(Dr. Maxwell K. Hearn)与孙志新先生(Dr. Jason Sun)给予的学术指导。本文写作与论证过程中,蒙李松、孟嗣徽、林伟正、左奇志等多位学者的指教与启发,使论文得以不断深化,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文/张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韩茂远,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美术观察)
注释:
〔1〕张见、韩茂远《在研究临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山西广胜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过程中的发现与推论》,《美术观察》2025年第4期。
〔2〕Hans Bel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Bod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
〔3〕Michelle C. Wang and Wei-Cheng Lin, “Introduction: The Performative Agency of Buddhist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Asia”, Art Orientalis 46, pp.7-12.
〔4〕柴泽俊、任毅敏《洪洞广胜寺》,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5〕Ellen B. Avrill, “Wenshu,Bodhisattva of Wisdom, at a Writing Table”, Chinese art in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 Cincinnati Art Museum, 1997, p.68.
〔6〕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国风》1934年第5卷第12期。
〔7〕无畏居士《广胜寺发见北宋錾经卷纪略》,《艺林月刊》1933年第47期。
〔8〕左奇志《原位、身份与图式——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元代壁画〈文殊图〉考》,《美术》2023年第9期。
〔9〕Ling-en Lu, “Pigment Style and Workshop Practice in the Yuan Dynasty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Lower Guangsheng Monastery”, in 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s. Nick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p.74-137.
〔10〕Ling-en Lu, “Pigment Style and Workshop Practice in the Yuan Dynasty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Lower Guangsheng Monastery”, in 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s., pp.74-137.
〔11〕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年第3期。
〔12〕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s,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595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Exhibition catalogue for the “Special Sale”, November 1, 1941 to April 30, 1942.
〔13〕Nina Leen, “C. T. Loo & Co. Liquidates”, 1950, LIFE Photo Collection, Time Inc.
〔14〕Lian Qu, Antiquity or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Mural in Southern Shanxi in the Yuan Dynas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9) p.127.
〔15〕孟嗣徽《20世纪初山西寺观壁画流散与缀合及相关问题》,《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16〕祁英涛、杜仙洲、陈明达《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17〕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1909), 1960 (English trans.), pp.21-25.
〔18〕柴泽俊、任毅敏《洪洞广胜寺》,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19〕Ling-en Lu, “Pigment Style and Workshop Practice in the Yuan Dynasty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Lower Guangsheng Monastery”, in 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s, pp.74-137.
〔20〕扈石祥《广胜寺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