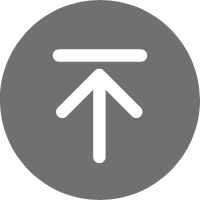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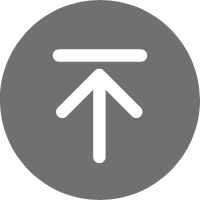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17年站在云冈对面的废弃矿井上遥望石窟顶上的凋残兵堡,想想此去不远的杀虎口,想想雁门关已在身后,是真的塞外了。想起金大侠的那一句“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牵衍出“千里茫茫若梦,双眸粲粲如星”的情长计短,烛畔旧盟,塞上空约,梦里真真语真幻。
六年后重到,这是拓跋珪的平城,昙耀的五窟,耿彦波的大同,华严寺、善化寺、法华寺、关帝庙,北魏明堂。那天九龙壁前的夕阳刚刚好。
从石窟出来,平传兄带我们参观他主持的云冈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室,三十几号人,蹭了研究院食堂的一顿免费午饭。
第二站太原,山西博物院,“何尊”前人不多,这里有最早的“中国”——猎猎旌旗下,荷戈的战士守卫着头戴王冠的人。青铜博物馆,从陶寺的铜铃,到二里岗、二里头、殷墟,鼎、盉、鬲、簋、卣、壶、钟,在青铜的幽光中,仿佛窥见商人窃窃私语的面孔,周人按不住了,遂有朝歌城外的血流漂杵,姬发远远望见鹿台上的纣王,穿着宝玉衣,跳进了熊熊大火中。
靖嘉非要请客,说要尽地主之谊,发了定位,一下车,晋阳会馆的匾额赫然在目,紧挨着,一墙之隔,“太原理工大学”六个字突入眼帘。天意弄人,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这是青主的一时逞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才是恒常世景。

从大同到碛口,仿佛过了半世。
凤临阁的百花烧麦和凤趴窝,鼓楼东街老火锅的二十五盘羊肉和大闸蟹,当众人在腾腾热气中大快朵颐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接下来没有油水的日子。有一个词叫“饿得慌”,说实话我就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词——没有身受,哪来感同,课堂上书本上的话,不落到自己身上,终究是别人的说辞。
碛口的第一顿,照例有一条黄河大鲤鱼,仅此一次,之后便绝迹。然后每天是各种混合菜,辣椒炒凉皮,洋葱拌饸饹,黄瓜老豆腐,各种不明材质的鱼豆腐关东煮,以及不放盐的蛋花汤。肉是稀奇物,有油,但没油水,吃完了,走到村口便饿。
11月5号,碛口最冷一天,下了一夜雨(老李说碛口下雨比上吊还难,我们赶上了),原计划去林家坪赶集。大家在清晨的寒风中等了半小时的公交车,26个座位,不能超载,于是分两拨。再半个小时,第二拨前脚刚踏上车,电话打来,说天太冷,集没了。半个小时后,我听到楼梯上叮叮咚咚的脚步声,知道他们回来了。晓凯探身问候,何承鸿回头撂下一句:“冻成孙子了”,饥加上寒,考验极限,好事。据说他们在林家坪最大的功绩,就是喂了一圈流浪狗,这也是好事。

下午出太阳,艳阳当头,仿似早晨的寒雨从未落下。三点约大家去爬后山,人不齐,估计是冻傻了,都在回血中。来的多是研究生,还是平时耐躁的那几个,人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
于我,则已是第五次登临。之前是野路,几乎是直上直下,却近,现在修了台阶,得从黑龙庙后绕,反而爬得气喘吁吁。十五年过去,荆棘还是荆棘,黄河还是黄河,人变了,每次上来的人都不同,加上新栽的小树,原先衰草满坡斜阳如血的寥阔大大打了折扣,心情也被切割。这座无名小山,是巅峰,也是伤悼,从地理到心理,是生命中一场至今尚未落幕的可念不可说。上一次登临,是和滕隆禹君班,一只形影不离的小流浪狗跟着我们一起爬上山顶,一起坐在草墩子上看夕阳慢慢湮落。寒烟,衰草,黄河,远嶂,天地有大美,因其有情,更有大悲。刍狗乎?草芥乎?不过是茫茫宇间的一粒尘埃,看看黄河两岸崖壁上的水线,沧海桑田,从来无关人事代谢。
夜深大寒,听到门外狗叫,呜呜哀戚,遂请进屋内,夜半醒来看它安静地趴在床脚,眼神纯澈,比人类干净。

此行硕士加上冠华的本科班,三十五六号人,中途冠华因其导师展览被唤回。本科班女生十之八九,仅有的两个男生似乎比女生更弱。晚饭后长聊,普遍的迷茫,给出建议:做好当下,增强主动性和行动力,提升工作量;锤炼心智,强化思维,保持敏锐度,保持判断力,保持行善的能力。
下乡,是从惯常的安全中进入陌生之地,见未见之人,遇未遇之事,广览博取,强健生命,以行启知,以知成人。所谓生命的游历,行万里路,是为成为更好的生命。
画道即人道。
2023年11月6号,当我站在白家山坡顶白晃晃的日头底下环望四方上下,乌鹊群翔,蛰虫秋鸣,仿佛千秋万代,四海列国,同此一景。
故乡归不得,归去非故家。
来日方长啊,同志努力。
(文/盛天晔 2023年11月12日)

游晋小记
回想晋岚萧瑟,快雨初晴,初到太原时难免心情振奋。不同以往几次满脑思愁郁郁而至,此行之前早已将身体与许多不悦之事收拾干净,得以抛下牵挂,只需想着游历,只需想着作画。走⼀遭后,踏过了更多险峻的山,喝了更多的酒,唤出了更多欢笑。⼀行人伤的伤,醉的醉,太多无稽之事想要记住,便摘了途中两篇日记,留给日后教训自己:
十一月五日登高,踏遍荆棘丛,臂膀皆挂彩,手脚并用“爬”上小小秃山⼀座。然登顶时山风呼啸,山⾳轰鸣,山岚萦绕,山鸟高飞,振奋异常。叹不至此无名后山,眺黄河残存之水举殷红落日者势必追悔莫及。
黄沙漫天,黄叶沉寂,残阳还剩⼀丝便要被群山掩去,面对余晖之叶如淤泥之下被遮蔽的赤金。老师回了⼀句“所以生命是自己走出来的”,便下山而去。
文字如钟磬般敲击,不似恒山顶的⼀览众山小,黑龙庙上的无名小山,尽是破土残坑与荆棘枝桠。但相较于车载至山腰、索道送至山脚的北岳,浑身解数周身挂彩地爬上这座山坡,其余韵反倒更为深刻震撼。俯瞰涸涩黄河滩涂,重峦围伏,风尘遮掩,湍急之水如被千手所托,坐困愁城。而此绝景非⼀步⼀脚印地踏破山土不可窥见其貌,为未至之人惋惜之余,亦为吃了这份“苦”而暗自庆幸。
虽流连忘返,然归去之时已到,写下数字,姗姗而去。
凌晨时分,无奈被唤去处理臭虫,去时郁闷而回时喜出望外。抬望天穹繁星游动,北斗猎户太白耀,启明众辰照星云。相背指认而寻天汉踪迹,忽瞥见流星⼀闪垂直坠于茫茫绛河,忙呼同行友人,但回头功夫已然又⼀流星划落,只留红晕烙在双眸。凝望良久,若似有蚕丝段段织起孤星点点,不自觉地便被星彩吸卷而入,许久未能平复。
春宵夜醉秋风月,几人欢笑几人愁。而人的小情小爱、悲怆恸哭,在头顶上这些悄然逝去的光点下竟是如此渺小,挣扎得如此叫人怜爱。纵使化作长河之中的⼀抹尘埃,亦想成为更为浓重,能冲击河滩、堆积河床的那颗。
星光没有暗去,睡意在一口长气呼出之后悄然袭来,稍作记录,解衣睡去。

绘画之事谈何容易,长命功夫四字足见其难于登天。而每次下乡登高,总会感到收拾画面变得⽐以往更得心应手了。翻越无名山岳,纵使路上荆棘伤人,深坑磕绊,但只需抬头爬起便能更进⼀步。此行深感人物画与登高无异,行者成,闻风丧胆而掉队者满盘皆失。即使⼀行人攀爬分缓急,登顶分先后,但行至顶峰,终将硕果累累。
而远眺星海,心中萦绕的烦忧思绪亦⼀扫而空,何事不可拂衣而去,何事不可快意恩仇?重重困惑皆为渺小之事,既然终将消逝,倒不如将心中山岳化作轻轻鸿毛,去攀绘画这重人生之岭。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会记住⼀辈⼦的可有可之事,以及同窗之间无需再反复诉说的肺腑之言,日后回想起必能开怀大笑,朝夕难忘。
回程路上怅然独坐,这趟飒沓北上、悠然南下的游晋之行恍然若梦,转瞬即逝。这是最快的一次,也是最快乐的一次下乡。
(文/李卓言)

两处废墟
“愿你还能认出更弱的声响,那是我们的影子在无穷地低语。”
——博纳富瓦《路人,这些是词语·······》
有一处声音传来,随后是一阵阵的低语绵延不绝。这些声音不来自于我们“即时”的现实,却被“即时成为的我们”所接收到——当时在镇国寺与双林寺的我们;在白家山与李家山的我们;在应县木塔、永乐宫的我们——都曾被这种絮语所环绕。在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存在的“即时性”被扣押了:我们不自觉地进入了它们的时间系统,这些“废墟”中任何一个细节所展开的时间切片,其丰富度都已经高过了我们的生命,那些绵延的低声絮语便来源于此。同时,这些“废墟”也如同一个中继站,使我们再次获得我们的“即时”成为可能。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罢了,因为我们都来自于一处另外的,已经完成的废墟。
这与任何的城乡或是信息控制差异都没有关系,因为当地人,从小孩子到在这些地方度过了大半生的人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同一处废墟:他们和我们都不处于(比如说,双林寺)当中的“绵延”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切片上。一个真正的废墟,即我们身处的废墟,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物。它不再产生任何声音与回音,所以也就更没有“绵延”存在。我们跋涉万里,来到陌生的土地,意外地走入了这处尚未完成的“废墟”。

当第一天我们走遍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时,皮鞋陷进了土里,在白色的板结的盐碱表壳下,泥土是一种温和的黄色;被荆棘划伤流出的血在裤子里结成了一个个暗红的小血块。倏忽间,黄河已在眼底。那一刻,我们束手无策,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去习惯这永恒的、低沉的河流的声音,去习惯这不平静的壮丽。在记忆中,这一幕被编织为了这些“废墟”的帷幔。当这帷幔被揭起,当这绵延中的无数时间切片开始诉说时,历史的压迫感终于足以将一个人击倒。这时,手机与相机成为了大家的庇护所,大家本能地躲在屏幕与镜头后面,让它们帮忙稀释着这些声音,直到所有声音与回忆都被稀释为二进制的视觉数据,我们才敢安心地低着头直视他它们,我们才敢玩弄般地在屏幕上操作放大、缩小,甚至加个滤镜。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强大的力量源自于真实。但他们忽略了一点,真实意味着已经完成:到那一刻,我们不会再从中听到任何声音,不会再感受到任何东西。它们会被如纪念品般重新建造起来,如同一张手机照片。它们未来的彻底毁灭-消亡将作为其在历史中达到自己完全真实的方式,然后它们便会作为总体真实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再被人接触到。
当我们在白家山的背后,在从未有人走过的荒原上摸索着开出一条小路时,突然随着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几只鸟从草丛中飞出,又随即消失在山坡背后。这时我知道,我们不该再手足无措了,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废墟里,一个微弱的裂隙出现了:我们在一条新辟的小路上,我们的现实还未完全闭合:可能性仍然在呼唤着我们。
(文/吕晓凯 2023.11.8夜于Z4284列车)

能重新大口呼吸是难得的体验,最大的感悟也许是对“生命力”的复得,一种回归最原始人的状态,最原始绘画的感受。如同山西的天气与地貌一样,淳朴简单。
——许嘉维
可真当我置身在黄土之中,荆棘条的确拽住我的衣服,划过我的双腿刺进我的皮肤,还有我一低头就是干旱的黄土,以及我一抬头就是让人睁不开眼的太阳,甚至那凛冽呼啸而来的北风,不留情得就像大浪一样一次次击打在我身上,害我被吹得踉跄了站不住脚,我才真正反应过来,我是真的在北方,在传说中的黄河,在真正的母亲河旁。
下乡,我认为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不再作为一个“当局者”的角色处在世间,而是成为旁观者”的角色来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 十四天里,青铜,佛寺,白桦树,石窟,黄河,山歌,荆棘,枣树,窑洞……日落西山,回过身,我们又回到了人世间。
——徐佩华
我喜欢太原晋祠的银杏,与钱王祠的银杏不同,在我看来也与自古对它们的一众美好寄托相左,它们是那么张牙舞爪,露着凶狠的脾气,要把冠子撑得再高些,再壮些,再猛些。下乡时,书上的历史静静地支在那儿,都并不沉重,面对带着各样情绪前去观看的人们,山西这片大地上的石窟、建筑、造像、壁画就那么千百年地支着,可以向天地间走来的每一个人风轻云淡地说一句“哥们儿,你来了?我曾经在这儿活过一回。”他们远比活人活得久远,也比活人活得精彩。
——鲍瀚文
我们面朝黄河远去夕阳西斜的方向,等待日落。不是我们在等太阳下山,而是要太阳再等等我们,阳光的消逝总勾起人的忧愁,他的余温将留下最闪耀的光景,光与热若退散,我们便只是孤冷的旅人,于是我们追寻落日最美的一瞬,也追寻内心的光与热。
——王靖嘉

今年下乡比往年晚很多,随之而变的是气温比往年更冷,早上冻完晚上冻。低温总给人失落的感觉。没见过黄河,第一次见,水并不如想象的湍急,很平静,但人是似火的,黄河给西北汉子养出了熏人的野味和热情。一时一地,回到文明社会的愿景不再像前些日子那么迫切,甚至想就在这偏僻的刮着风的黄河边暖洋洋的石板上躺到死,也没机会了。
——赵晟
在赶集时看到的老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动笔后才发现他们情绪饱满畅所欲言,聊到激动处更是手舞足蹈。。。。。。双林寺,即使已经见识过她的精妙绝伦,重逢瞬间给我的震撼依旧直击心灵。
——张琳
动物出现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带着他们干净的眼神和逆来顺受的姿态。我们在逐渐失温的城市里结伴回家……白天所见的各种古迹山川和众生面孔,又让我们显得格外渺小,真正变成了宇宙经纬交汇无限小的小点,变成了黄土高原上的一粒沙石。沧海桑田的变化在时间面前也显得不值一提,但人生几十载也可以见证很多,那就希望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希望自己画出一件张在时间面前能站的住的画。
——刘云霈
用双脚丈量大地,站在天地之间方知一个人是多么渺小。画画的人首先要面对自己,才能面对众生,但现在的我得先学会面对自己,至少要对得起自己。
——田野风
在这里,时间凝固砌成石墙砖瓦,岁月沉淀化为尘土砂石。在五天一次的集市上,把头伸出窗外的车主、见缝插针的电动车后座的小孩,一动不动坐在石阶上观望马路的修鞋匠、被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得意洋洋打着扑克牌的人……而我们也知道,“体验”是短暂的。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和深入这片土地,还远远、远远的不够。
——陈欣
再回到碛口,黄河边的晚霞恰如生与死,爱与恨的交织。画者,应当是天地之心,你为什么而生,你以什么样的姿态生存,还得是自己去造型。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经纬度,这或许就是下乡的最大意义。
——王冠杰





下乡写生作品

作者:盛天晔

作者:盛天晔

作者:李卓言

作者:李卓言

作者:李卓言

作者:王靖嘉

作者:王靖嘉

作者:刘云霈

作者:刘云霈

作者:赵晟

作者:赵晟

作者:张琳

作者:陈欣

作者:鲍瀚文

作者:鲍瀚文
(来源: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画家简介

盛天晔,1971年2月生于浙江鄞县。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第五届中国画艺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写意人物画教学和研究,师从刘国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