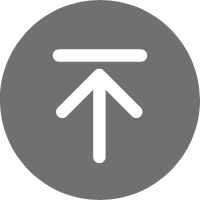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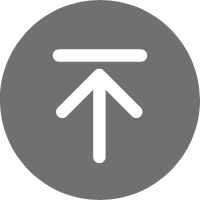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炽热丹心浓浓情
李富胜
《蔚蓝色的记忆》是一部难得的散文集。读后,仿佛一缕清风拂面,爽快惬意而情愫激动。其作品集,以深厚内涵的景物事实,生动鲜活的艺术语言,凝生“形散而神聚”的散文特质,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意识境界。品读作品,激情被点燃,灵魂亦释然。
谋篇布局,《蔚蓝色的记忆》精致巧妙,合情合理,顺畅达致,可见作者深思熟虑的思考和细致精道的理性思维。整部作品共分“山水清音、古村探幽、滋味荣成、人物素描、蓝色记忆”五个篇章。每个篇章尽管表达的主题思想各异,但每篇文章都有着高品格的韵味和灵性飞扬的律动。山水翠碧,草木萋萋,村落炊烟,海岛气象,大海波澜,往事云烟,渔夫村姑等,逻辑思维架构搭建严谨,形象思维描述生动。栩栩如生、活龙活现、精彩洒脱、自在落地的文学艺术性,融汇贯通于每一篇文章,引人入胜,动之以情。
著名的散文作家梁衡先生提出,散文的审美创作,必须正确把握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审美的作用即艺术对人的作用。并强调,艺术创作不能媚俗,应当承担净化心灵的责任。细读《蔚蓝色的记忆》,可感悟作者在创作中把握的艺术逻辑,是如此严谨,作者通过主体对客体的认真审美,研究、欣赏、提升其艺术价值,使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人与审美对象互融渗透,作品所产生出的正能量,对人的感染熏陶作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作者驾驭创作能力,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通读整部作品集,内容丰富厚实,内涵深邃博大,艺术极致臻美,是作者“见所见而见,闻所闻而闻。”通过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用精致的审美意识,用超然的心智去悟道体会,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飞跃,形成了艺术的敏锐思维,以强烈的创作欲望去实现创作的理想。其作品,上下通泰,内外通达,从中看到事物的多层面,多元性,甚至更深更远。
“情”动的咏叹,至真至美,照亮心灵和现实。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是作品集最显著的内涵特质。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情的咏叹,奏鸣了一曲大情至诚的散文交响,震撼人心,感人五衷。作者以一颗炽热的心,燃烧着自我的情,倾诉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对亲人友人乡亲们的真诚大爱,对蔚蓝色大海的依恋。正如作者序中所言:“我爱家乡,亦爱大海。走了这么久,才发现,最终的皈依,依旧是最初出发的地方。从源头开始,在具有海味的文化体系中,用文字跟踪自己,关注着自己,不断拓展边界,在关系里看到自己对世界的解读,看到世界对自己的观照,这是生命的成长。”作品是作者情感的真诚释然,用真情倾诉真情。《父辈的村庄》中,用细腻的笔触,道出父辈在历史交替变换中的那份纯朴实在的情,父亲在拆除了老村庄和新楼房建起时,那种矛盾情感起伏跌宕的纠结,让人读懂了父辈的对生养自己老村庄的那份难舍眷恋之情,“父辈的村庄,在新旧胶片中,都那么底气。”浓浓乡情,是厚重的,散发着海的味道,浸着风雨的苦涩滋味,透着自然风物灵性,刻着历史的印记。诸如,《自在花村》、《留村》、《韵味东楮岛》、《凡尘清骨圣水观》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对乡情的纯朴真情实感,诱人向往。
文学语言的精巧描述,生动鲜活,引人入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形象生动的表达,必须体现美的语言内涵和特质。散文最为重要的精神实质,“形散而神不散”,要达到“神聚”的高度,其一立意,其二语言,两者互为照应,方能彰显效果。《蔚蓝色的记忆》之所以让人感佩,其中形象语言之生动鲜活,让人耳目一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实为一大个性特点。作品的语言,咏物寄情,飘逸洒脱,抒发情怀,奔放气昂,文如流水,语似冬阳。纯美的语言风格,为作品的灵透,增添了异彩纷呈的艳丽重彩。《父辈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段描述:“母亲的心意,父亲一直都懂。母亲没有机会住进楼房。我们都知道,父亲的心里,一直住着母亲的心意。”一个“住”字,用的如此巧妙,把父亲与母亲那种默契和挚爱,用一个“住”表达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韵味东楮岛》作品中,对“韵味”的细腻描述,可以说是点睛之笔,精致巧妙。“东楮岛的韵味在于一个“咸”字,咸,于东楮岛,是一种风情。咸咸的海风,是迎宾的女郎,用一颗温润的心,浸润了路尘而来的客人。海,是楮岛人的粮仓,丰盈的海产品资源,演绎了一出出舌尖上的浪漫。”这形象的描述,气氛渲染,美不胜收,其美令人神往之。另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区域方言,有较大的亲切感,也是十分精巧,雅俗共赏,趣味兴然。“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
引经据典,精准到位,作品厚重而沉稳。运用引经据典的艺术手法,是散文重要的技法之。能运用好,也是不容易的。著名散文家梁衡于2001年7月,在鲁迅文学院讲授《文章五诀》,将文章写法归结为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其中形、事、情、理是文章中不可缺少,也就是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内容,又是描写、叙述、抒发、议论四个基本手法。“典”就是运用经典。从整部作品中,可以品读出,作者运用《文章五诀》技法娴熟灵活,是讲究散文章法的。从作品中还可感悟到,作者在用“典”上可谓高手,引经据典,严谨细致,得体明晰,逻辑透彻。诸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道德经》中有言到,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补。”“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家正则天下治;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身正而家治,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在用典上,细致讲究,恰到好处。在作品的关键节点上,用经典佐证概述,增加了厚重感,用理性思维助推形象思维飞扬,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蔚蓝色的记忆》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精神内涵和艺术表达,都不失为至臻达美。意境美,语言美,哲理美,都是精致风韵,质朴佳作。古人云:一事精致,便能动人。读其作品,犹如身临其境,文润其身,自得芳华,受益匪浅。
梁翠丽是一位成熟理智的作家,她是一位大学教授,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丰富,善于思考,是高水平境界的学者。但是,她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已经出版两部散文集,荣膺过多种文学奖。这都是她努力奋斗的结果。她对文学的追求是执着坚韧的,她保持着一个非常明静的心态,拥有两只敏锐的眼睛、一双勤劳的手、两条奔忙的腿,一种永远阳光、平静、自由的心性。励志进取,执着追求,明天光明,未来灿烂!梁翠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人!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拙笔

李富胜
山东威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被中央文明委、人事部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工作者,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其中由长篇小说《天边有个威海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0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广播剧《为了孩子》、《那片蓝蓝的海湾》获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创作的歌曲《领航中国》(与曲波合作)入选国庆60周年演奏曲目和惟一领唱歌曲,《你和人民在一起》《甲午祭》(与曲波合作)获泰山文艺奖。
附:梁翠丽散文两篇
《海草房》
作者:梁翠丽
家乡的海草房,充满了梦幻般的想象,始终以一种独特的背影印在时光的画卷里,成了渔家儿女生命的图腾。
在胶东半岛,尤其是威海地区,以荣成为典范,海草房成了一种标志性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那些“从海里长出来的房子”,是渔家人温暖的巢。
它们,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魅力,带着某种特定的气息和场景,在岁月的万般风情中,挺立、傲然,然后发酵成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炊烟袅袅中,蜕变、扎根;扎根、蜕变,演绎着渔家人千百年的沧桑。
生于斯长于斯的渔家儿女,对海草房有着不一样的情感。那些灰白、灰褐的海草啊,是开在海里的花儿,受了海的滋养和熏陶,上得岸来,成了人家屋顶筑巢的烟萝,带着千百年大海沉淀而来气息,沉静而优雅。它们,柔软地团在屋顶,以柔韧的身躯,遮挡了海风的肆虐,海浪的侵袭,给渔家人以生的安养。
海草房是风景的,更是烟火的。每个渔家儿女,都有同样的感受:无论多大的风浪,站在海边,不必担心,身后有那些温暖而实在的海草房,足够力量;心,必定踏实而放松,不离不弃的海草房可随时随地纾解一身尘埃。
渔舟唱晚,走进海草房的院落,极容易看到有男人在剖鱼,粗糙的大手,黑而壮,却不乏灵巧;女人们则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炒菜,习惯性地裹着头巾;刚下船的男人们,拖着胜利的渔网,喜滋滋地彼此调侃:张家的孩子调皮,被老师揍了屁股,李家的女人越来越漂亮了,赵家的猪下了一窝猪仔;还有那些在街口蹲墙根的老人们,岁月的风霜,大海的扰攘,已将他们的脸晒成了独特标志的“海风红”,甚至拖着鼻涕迎风流泪,偶尔用袖口擦一下,不动声色地看着放学归来的小孩子。
粗粝、生动、平静,这就是海草房极为原始的生命态,不惊艳,却有攻城略地的气势,迅速占据了每个过往者的心。
那一些有生命温度的房子啊,安静中,就倾了城,倾了国。
犹记得小时候,海草房是孩子们的乐园。多数海草房,与家里的厢房或者是平房相连,爬上房顶,并不困难。春夏之际,海草房上长满了一种叫做“饽饽指头”的植物,后来查了书才知道,这种植物有个文质彬彬的名字,叫“瓦松”。
这种植物,寄予了顽强抗争、生生不息、特立独行的民族精神,被历代文人唱咏,留下了许多俊朗的篇章。唐代诗人李晔《尚书都堂瓦松》咏瓦松的诗:“华省秘仙踪,高堂露瓦松。叶因春后长,花为雨来浓。影混鸳鸯色,光含翡翠容。天然斯所寄,地势太无从。接栋临双阙,连甍近九重。宁知深涧底,霜雪岁兼封”,表达作者寄居高位处庙堂之上的文人心志。但在孩子们眼里心里,是极为普通的植物,只因为样子特别,且通常长在房顶上而额外被关注。
每到仲春,万象更新,瓦松琳琅的海草房格外蓬勃葱郁。一群孩子,相约拿了梯子,爬上房顶采来吃,味道酸酸的,有种青草的清凉。医书上说,瓦松药用价值极高,是难得的降血压的良药,那时候对此全然不知。而秋天,瓦松便不能再吃,海草房的狗尾巴草,又成了孩子们稀罕的玩伴,通常会被采下来,编成小兔子或者小花猫。狗尾巴草不独有海草房上才有,可似乎只有长在海草上的那些狗尾巴草,才能引发玩乐的兴致。
当然,这也是要瞒着大人们的。海草房固然可以扛得住孩子们的折腾,可一旦弄乱了屋顶的海草,透了泥坯,也会漏雨,更何况爬上房顶玩耍,也危险。
最难忘的,便是冬日。窗外清雪飘零,海草房把朔风的凛冽减弱到最轻。屋里烧了大炕,暖烘烘的,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人围桌而啖,母亲烀了豆面粑粑,炖了青鱼,熬了地瓜粥,做了萝卜丝豆沫球。平和安适的温暖就着幽暗的灯火一点点蔓延,个个脸上都是笑意。父亲在饭后的灯下,泡一壶地瓜叶子样的粗茶,仔细询问我们一整天的情况,说的最多的是,今天的作业可曾用心?今天干活可曾尽力?问姐姐最多的便是,可曾照顾好弟妹?我们一一作答后,不管答案是什么,父亲均少评判,只是象征性地结束了这个过程,接着会教我们一两句古诗。虽为教书人,父亲血脉里滚动的依然是渔家人豪迈,之后多年,我能记得下的诗句,多半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豪迈诗句为主。
海草房,就在这质朴而简单的生活中养育了海味文化。它周身也透着厚重的诗性-----超然、挺拔,从远古走来,平仄之间,全是内涵。有承担,有魄力,一笔一划,一步一步成就了了渔家人大巧若拙的文化特质:风日洒然,豪放浪漫!
而印证这一切的,便是那些蹁跹而来的天鹅。
在荣成,有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成片的海草房,成了天鹅们依恋的家。每年冬天,那些踏雪而来的天鹅,和生活在海草房里的渔民一起,迎接冬至春来的时光盛宴。
天鹅、海草房、渔舟、清雪,这些景致在一起,超视觉的享受,如梦似幻。海草房的沉稳安静,与天鹅的灵巧生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任是才华横溢的画家,也难描摹其中一二。慕名而来的艺术家们,放下了手中的画笔,成了人们镜头下极为和谐、极为烟火的一幕。他们,成了海草房的客人,也成了天鹅们眼中的风景,偶尔一激灵,振翅翱翔,便是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的欢迎。
千百年来,海草房成了渔家人的留守者,为世世代代远足的游子,守住了回家的灯塔,也为世世代代在家的孩子,淡定了气度,成了渔家人无法漠视的符号,在满眼的浮世富贵中,素成一种美的极致,被一些有心人铭记。
表弟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有着极为浓烈的海草房情结。悉数十多年来,他一次次为海草房倾尽所有,我经常觉得他的渔家人气质特别鲜明。说起海草房,他眼里总是有光。他说,一个地区总得有自己的文化代码,咱这里就是海草房,它好看又实用,还被制成邮票,全国都有了记忆,这有多独特。我们世世代代都从海草房里长大,骨血里有海草的味道,那些房子养育了多少渔家人,没人说得清。说远了,我们的将军县,我们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蓝色基因的传承,不都得益于海草房么?更何况,海草房多美,从不咄咄逼人。
是的,海草房是安养的,有神的,有生机的,从不咄咄逼人。因为这么有善意、有灵魂的房子,他做了一片以海草房为主题的“康养小村”,我一走进那小村,眼泪就下来了。那般的平静,那般的柔顺,那般地烟火从容,似乎逼出我所有的成长记忆,一幕幕牧渔耕海的画面瞬间在眼眶里打转。
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份美,也是因为有了人的用心,才会彰显。因为表弟深深文化情怀,因为他深嵌在一花一木、一草一瓦的深情,才有了如今的“海草湾”------哦,那是一个连石头缝与泥墙上都有他,一个渔家人心意的、新时代的、小众的,又极为深情的地方。
在一个钢筋混凝土丛生的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为信息裹挟,很难分得清,真正愉悦我们的到底是五光十色的城市霓虹,还是那些缓慢的、平和的、没有霸凌的,发乎天然且由时间浸润出的记忆,更加令我们会心。
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表弟,那个曾经在我们姊妹爬上房顶摘瓦松吃时,只能眼巴巴地在地上等着的小孩,长大了。他用自己的心,默默地在时光里黏起了那些海草与石墙;用自己的情义搭建了渔家人精神返乡的长久路径,塑型成长记忆。那片在高楼林立中默默生长的海草房,就像所有渔家人曾经的日子一样,素朴、阳光。虽在城市灯火中,并不起眼,却持续、长久又瓜瓞绵长。
我坐在表弟“海草湾”的一栋海草房的露天平房上,闻着远方潮涌起来的阵阵海风,望着在阳光纯粹的瞩目中那些散发着光芒的喑哑的海草,不觉感慨万千。不得不说,有些光芒,有些美好,必是哑光状态下,才被看得见。
细数那些海草房的村落吧,齿颊之间,覆满风烟,念读起来,绵远悠长。烟墩角,大庄许家,巍巍村,东楮岛,中我岛,留村……每一个村落,念起来,都是长长的一段历史,长长的一段故事,长长的一串温情。低回,饱满,内敛而坚硬,在时光的画卷中,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背影。
每个游子,思乡的理由,都是那些有生命的房子;每个渔家儿女,热爱的理由,就是那些有厚度的、温暖的海草房。
《父辈的村庄》
(一)
父亲笑得像个孩子。
父辈的村庄,成了楼房;父辈的村庄,升了级,改了版,这是村庄里一年最大的事情。
迁入新居第一天,父亲脸上的笑容没有间断,只有在念叨母亲的时候,眼里才会有一丝落寞与水雾。
楼道干净,脚底没有尘土飞扬。亮白的墙,闪着柔和的光;泛着古意的中式装修,透着儒雅;阳台上,是父亲母亲钟爱的花草;宽敞的书房里,有父亲存了一辈子的老书;卧房里,依旧摆放了母亲生前的旧棉被。父亲说,母亲总是喜欢用稍旧一点的被褥,有日子的模样。
父亲说,住进楼房,是母亲一生的愿望。母亲爱干净,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母亲打扫尘土的身影,成了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标识。母亲愿意住进楼房。她说,干干净净的,日子才能过得安心。
母亲的心意,父亲一直都懂。
母亲没有机会住进楼房。我们都知道,父亲的心里,一直住着母亲的心意。
退休之后,父亲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候鸟”。在城市里居住的父亲,并不心安。他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春耕秋收,只有白雪皑皑的冬日,他才蛰伏在城市的楼房里,等候着春天的到来。
终于,在父亲和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村庄,拔地而起一座座楼房。村庄,成了隐喻,渐行渐远。可父亲说,乡愁是骨血,矗立的楼房是村庄的骨骼。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活法,父亲愿意与时俱进。
平地升起的一排排楼房,我记忆中的村庄消失了。
父亲的晚年,住在属于村庄的楼房里,干净、便捷、通透。一村庄的人都住上了楼,欢天喜地的,和小时候过年一样。父亲说,他看到了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村庄。他记忆中的村庄,是母亲为雨天家中夹带的泥土无法清扫干净的郁闷;是奶奶一声高过一声的要求清理厕所粪便的急促,是蚊蝇永远祛除不绝的叨扰……
父亲的话,让我儿时的记忆泛潮。记得曾经的村庄,每次去厕所,必定要拽了母亲去赶蚊蝇,母亲眼神中,多有无奈。
把母亲的画像挂在了墙上,希望她看到新居的敞亮。我的眼角却清泪四溢。父亲的心愿就是母亲可以住在楼房里,听他侃那些她听了一辈子的老故事……
(二)
父亲站在被拆损的老屋前,莫衷一是。
时值初春。沿海的风,在这个季节,总是霸气又顽固,不肯轻易离场,搅得春意阑珊。破碎的瓦砾,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海草房上的海草,被扯得东一块西一块,还是不肯分开,彼此纠缠着,成片成片地飞扬;老屋前的榆树,一丁点的绿意也在飞蓬的寒意中,瑟瑟发抖。
村庄被拆了,几乎在一夜之间。
看得出来,他有些落寞。他说,半辈子住在这里,爷爷奶奶的影子都留在了堂屋,他忘不掉。檐前的燕巢,颓败凋零,巢内不见燕子啁啾,燕子也知道要搬家了。
他的记忆停留在曾经。每年乳燕归巢,他与伯父就散了欢儿地往地里跑。辽阔的土地,清新的空气,一浪压过一样的绿意,装点了他的童年。夏日里,有知了嘶鸣,更有蟋蟀唱和。奶奶总是在俩淘气的男孩子各种恼人的玩闹中,发着脾气。甚至为了清净,捣了燕巢,可那些燕子啊,为了孩子们的喜欢,依旧会再筑新巢。
我犹记得儿时堂前有好多燕巢。父亲从不捣燕巢,更不允许我们随便叨扰那些飞来飞去的燕子。父亲说,一个屋子,没有了燕子的啁啾,是少了生机的,燕子愿意在那些祥和的人家檐前筑巢,这是生命间的一种肯定与契约,更何况,没有了燕子,孩子们的生命怎么会仁爱起来呢。
墙角依旧堆满了旧农具。父亲拿起一把铁锹,锈迹斑斑,满身都是岁月。父亲说,这把铁锹,是爷爷那辈儿传下来的。他读书,做的农活少,可伯父用这把铁锹很上手,伯父说,这铁锹,有爷爷的力量,再苦再累,手中有了这把铁锹,心里就扎实。那是爷爷从他的父亲那里接过来的,据说,是家里一把经得起时光检验的铁锹,坚固耐用,父亲不知道它已经历了几代。
门前有捣臼。父亲擦了擦落在上面的灰尘,说,捣臼也有年岁了,他记事的时候已经在了,现在成了古董。有人来收这古董,父亲没有犹豫,很少的钱就卖了。我说,其实可以再贵一点,那里面也有我们曾经的记忆。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浅秋的日子,坐在捣臼里,望着漫天的繁星,听奶奶和父亲讲那些听了又听的老故事,关于狐仙、关于牛郎织女、关于炎黄大战……
父亲有些眷恋。
我理解父亲的眷恋。这栋老屋,他从祖父哪里承继过来,虽年久失修,几经修缮,斑斑驳驳的墙,好像一块布上的补丁,并不好看,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记忆,并没有损毁多少,反而随着岁月的递增,多了怀想。我的记忆,亦有一部分在老屋。拆了一栋屋,就拆了曾经的记忆,生命就有了断层,这是心理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如同血脉。
又有人来收各种旧物。父亲卖了铁锹,卖了瓦罐,卖了小推车。那些有了记忆的老物件,父亲没留。
他说,什么都会变成古董,包括这老屋。人一辈子,不能纠结抓到手什么,要看到那些没有到手的,那才是新生,才是力量。更何况,没什么总是自己的,最紧要的是要懂得放手。
我信。
父亲是个豁达的人,他那辈人,都疏阔,有魏晋风度,亦有宋明恬淡。父辈们的心意,在曾经的土地上,种下了种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鲜亮的生机。
父亲说,这是真的传承,不是守个旧物件不断哀悼。生活,要高亮,像大红袍那样,高亮。
我与父亲站在即将拆除的老屋前,呼吸着属于各自时代的空气。看得出父亲内心的复杂,亦看得出父亲眼角的期盼。有风来,父亲擦了擦眼角,说,总要更新换代的。
我与父亲,在老屋前合了影。未来,这里将诞生大片新楼房,母亲的遗愿,就要实现了。
(三)
老屋后街的邻居伯父不肯搬迁。
他是个文化人,是个考古学家。半生的漂泊,他最终选择了回老家安度晚年。他喜欢宅在自己的老屋子里,盯着那些陈旧的古董发呆,一盯就是一整天。他常说,那些古董都是有故事的,每一件老物件里的情谊,都无法取代,每一个物件里都藏着时间的秘密,与它们交流,有无限的乐趣。
他的房子陈旧、破败,甚至漏风透雨。不抚摸古董的时候,他多半时间修补房屋。今天找点黄泥像个瓦匠一般地贴一下土墙,明天找几把草,上了屋顶,修补那些被风雨掀飞的海草。草长莺飞,时间在他那里,是和老屋相携相伴的。老伴儿多数时间,怀疑地看着他节奏笨拙的忙碌,眼神里的静默,能沉出水来,谁也看不出态度。她,已经半瘫了。
拆迁工作组来了一拨又一拨。得到的答复总是说,我愿意住楼房就不会回村了,回村了,就是让身体发肤,接近土地,有人气儿。工作人员以照顾他老伴儿为理由,劝导他同意签署拆迁协议。他不签,说,老伴儿签他就签。可老伴儿,永远静默宛如雕塑。
在轰隆隆的拆迁中,他偏居一隅,独自。院墙里,四面透风,院子里有棵古旧的杏树,春天花开繁盛,墙内墙外都是花儿。他把老伴儿搬出屋子晒太阳。院墙的边角处,养了鸡,母鸡咕咕叫着,他坐在满院子的瓶瓶罐罐边上,嘬口老茶,拿一把放大镜,津津有味地与他的“宝贝们”聊天儿。他的老伴儿,眯缝着眼睛,盯着盛开的杏花,偶尔一笑。
全村的楼房拆得差不多了。他的屋,成了“孤岛”,没有了邻居,院墙四周施工的隆隆声,搅得他失去了宁静。他不能随便搬老伴儿出来晒太阳了,母鸡不叫也不下蛋了,天天猫在窝里,警觉地看着来往行人。他出门,来回游走在那些被推到的瓦屋破败的墙土中,盯着那些被翻新后的土,一家又一家,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气息,眉头越皱越紧。长长的落日下,他单薄的身影,拉得老长。
那天,他叫了父亲去他家一起喝茶。
父亲说,搬吧,换个环境,会更好。村庄的楼房,不同于城市,他还会拥有自己的“守乐斋”,那是他安放古董的屋子。
他只是摇头,说,味道变了,感觉是不一样的。
父亲说,古往今来,都在变,他的古董写的就是一个“变”字。
那一天,他们甚至喝了一点小酒。“守乐斋”里的那些古董,第二天,就被人帮忙搬运到为他临时准备的存储室里,秋毫未损。
又一个杏花盛开的日子,他也搬进了楼房。是一楼,连同那棵有记忆的杏花树。
楼房里,依旧有“守乐斋”。全部的收藏,悉数归位,且条理清晰。父亲打趣说,这些古董都见了光,有了光明的样子,格外温润。遥想那些曾经拥有这些物件的主人也是希望被如此善待。
他脸上有了光,和那些古董一样,还有他的老伴儿,那个始终没有态度的女人,脸上也有浅浅的笑。
他把老伴儿搬出了楼,就坐在那棵杏花树下,杏花树旁边,多了很多不一样的花木。
他嘬着茶,拿着放大镜,依旧揣摩那些古董。那个曾经表情不丰富的老伴儿在暖暖的春日下,满脸的笑意。不远处,村里重新规划的健身公园里,一群孩子咯咯地笑着、闹着,惊起落花阵阵,花香一时之间,随着风,飘了满村。
(四)
伯父躺在病榻上,满脸笑意。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世上待多久,我们亦不知。可我们知道伯父的心愿,他要住进新楼房。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伯父,与父亲的清雅相比较,他更朴直,更敞亮。
同后街伯父一样的村庄人,很多。不愿意搬出老屋,不愿意丢掉曾经的记忆。伯父并不是村干部,可伯父坐到了人家的土炕上,不断诉说着他去“大城市”几个女儿家居住的体验:晚上去厕所不用出门,冬天不会冻屁股,夏天不会有蚊虫,家里不会有尘土,用水不用肩挑人抬,堂屋永远都亮堂,卧室满处可见阳光。他孜孜矻矻地游说着与他交好的朋友,与他一辈子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农人。因为伯父良好的信誉,大家都信了他,同意搬迁。伯父把村里的搬迁大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他年迈,患了绝症。可只要村里人搬迁过程中有困难,必定第一个跑去帮忙。他说,不能总局限在自己的小日子里,外面的天大着呢,得拉着大伙一起往前看;他又是个急性子,搬迁期间,住在堂姐家,总是身不由己地逼着堂姐送他回来看村里改建进程。
在盼望中,他的病情不断恶化着,终于不能再回来“监工”。村干部说,老人家就是这村里名副其实的干部,有了他,很多工作顺理成章。
病榻上的伯父,不断地对我们说,不喜欢医院的味道,不要给他插大大小小的管子。那是对他的糟蹋,他的楼房,他的村庄,才是他的归宿。
厚道的村庄人,知道老人的心意,特意开了绿灯,抓紧赶工,为老人装修好了一栋楼,在手续尚未齐全的情况下,破例让老人住进了新楼房。
伯父住进了自己的新家。奄奄一息的他,仿佛得了某种力量,一下子精神起来。摸摸床,摸摸玻璃,搬个小凳子,坐在落地窗前,满屋的阳光洒进来,屋内的绿植,很有诚意地绿着,如在山里一样。伯父的神情安然,几丝银发矗立,闪着太阳的光亮。他笑得像个孩子,说,新旧对比,现在的日子,过得像神仙,他想活着,多过些好日子。
看着他笑,我们心里却惴惴。我总和他说,要好起来,等所有的花儿,都开了,就带着他逛遍全村。长在村里的那些花草呀,一点也不比曾经的他劳作过的田野少。他说,好,要看看村里的变化。
那一天,他看了报纸,说报纸上有我的报道,要伯母打电话给我,要与我聊聊我们家族的故事。
我去了,他精神特别好。说住进了楼房,我们家族,很有机会复兴,嘱我查看族谱,祖上曾经是翰林院士,顶级的读书人,这么好的日子,要慢慢过,要向祖上学习云云。
没有来得及给伯父交上圆满的答卷,没有来得及听他细说往事,伯父走了,那时候花儿并未开全。寂寞的冷,如同我们一家人的心。伯父脸上挂着笑意,他住进了楼房,安静地离开了,像是睡着了一般。
父亲说,伯父没有遗憾。他在地里劳作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住进楼房,在村子里,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五)
新年。
父亲在楼房里找了单间屋,供奉了族谱,叫我们重新背诵了家训。伯父与母亲,都在族谱上留了名、留了像。
我们虔诚地礼拜着,希望他们看得到如今的村庄。
恍惚中,我似见到了母亲。她慈爱地在每个屋里走,依旧勤劳,依旧默不作声地从一间屋到另外一间屋,不断地清扫着卫生;见到伯父,在村头的槐树下,坐个马扎儿,笑意盈盈地和村里的老人聊天儿……
属于父辈们的村庄老去了。时光一轮又一轮的变迁中,村庄变成了以楼房为主的农民聚居地。
有人敲门,村里人来拜年了。父亲也叮嘱我们去村里的婶子大娘处拜年,父亲说,村庄换了形式,可乡情没换。
我们一家家地走,一家家地看。相似的建筑,不同的人间情怀,在新的村庄体系中慢慢形成。
有孩子放鞭炮,家长叮嘱,要扫干净了,免得脏了村里的甬道;有人随便扔纸屑,立刻有人提醒,这不是老村庄,不能随地丢垃圾,村子要和城里一样干净;下了清雪,家家户户拿了工具,瞬间清扫干净。老人们说,别丢了村里的“份儿”,叫人笑话是“土包子”。
村里的文明,成了村民们自觉的事情。没有人教育,仿佛一夜之间,村里人多走了几十年。
入夜。家家户户在新年的祝福声中,燃起了灯火,村子一片光明。端了一杯酒,敬父亲。父亲说,他喝,新年新气象。
我在父亲的眼角,看到了一些闪光的东西。新的村庄,在一代人的凝望中,凸显出毫无修饰的真实。
父辈的村庄,在新旧胶片中,都那么有底气。

梁翠丽,女,山东省作协会员、荣成作协副主席。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散文单篇多次获奖,其中《一个有长度的季节》发表于《美文》,后被被作为中学考试阅读题被广泛转载;散文《留村》、《一座山的回响》等多篇发表于《四川文学》《时代文学》等刊物,出版散文集《一路花开》《蔚蓝色的记忆》;2016年被评为“威海市文化名家”。现供职于威海海洋职业学院,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与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