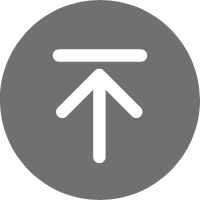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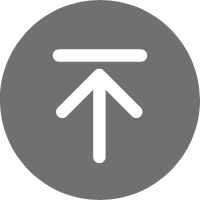

吴门画派是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鼎盛于明中期即孝宗弘治初年(1488)至穆宗隆庆末年(1572)的一个绘画流派。沈、文、唐、仇等人,在折衷院体画与文人画的基础上,各秉己赋,或以元化宋,或以宋化元,形成自家文雅蕴藉、沉静柔和的画风。其流风所及,汇而成派。上承宋元,下开松江,是中国文人画史上的重镇。为日后文人画派在题材选择、师承渊源、艺术风格,以及精英化的人员组合和新风尚的开拓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吴门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沈周。他因教导出了诸多在画史上有地位的学生,而被后人推为该画派的开创人。然而,吴门画派的孕育及生成,虽说应以沈周的活动时间来参考划分,但若定为明前期,有着明显的偏颇。我想,画派应以文徵明、唐寅等人在画坛的崛起为标志,崛起之前的时间为孕育和生成期,崛起之际为鼎盛期。下延效法成风时,所谓画派才能够正式形成。
我们可以沿着时间表来分析,沈周生于明宣德二年(1427),历经明前期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至成化末年(1487)。这期间(60年),沈周的各种活动当属个体性行为。明中期自弘治初年(1488)至隆庆末年(1572),以文、唐、仇等人集体创作的成功为标志而形成画派。按史载,明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中解元,仇英出生(约1498),嘉庆二年(1523)文徵明入翰林院、授待诏,仇英25岁,唐寅卒。即1498年至1523年为形成期。自1523年始,期间陈淳卒(1544),沈周卒(1559),陆治卒(1576)。可以确定1523年至1576年,是吴门画派的鼎盛期。自万历三年(1576)吴门画派逐渐衰没,1610年左右,被松江画派所替代。
为什么说是1610年左右,松江画派取代了吴门画派的画坛盟主地位?这是缘于董其昌23岁方从陆树声学山水;37岁后,始力追唐宋;50岁时自谓大成。所谓大成,当指他有自我风格和相当影响力而言(包括官位)。故而松江取代吴门以1610年为界限划分比较客观。否则,在此之前,以董其昌为领袖的松江画派,有何能耐主盟画坛呢?

在贴切于其时代与事理考察,纠模棱两可的史说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沈周话题上,评谈他及其吴门前辈画家,为吴门画派形成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明朝是中国画史上画派迭起的朝代。在依托城镇经济繁荣、消长为起落的前提下,自浙派始,相继产生了吴门、松江、武林、嘉兴、姑孰、武进、江宁等画派。特别需要明确的是画派的产生,首先以地域划分。其次,才以风格来划分。从其产生到纷立的历史事实亦是如此,我们不能脱离史实而言他。以风格来划分,是后来的理论家以精英者组合,相互标榜、上攀下附的说法。其说始者,当为莫是龙、董其昌二人。
第一个名著中国画史的流派,是浙江画派。在此之前,中国画史中没有被正式命名的画派。“画派”一词的出现,向人们发布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以个人图式、独立名义,宗主中国画坛的历史结束了。自兹,画坛的宗主法则,已改制为诸多人员配合、团体联盟的方式结成派别、参与竞争。其胜出者,是以画派的名义主盟画坛。
其实,这种局面的出现,当追溯到元代。赵子昂虽说是元代的画坛宗主,但其宗主形象是模糊的,诸如钱选、高克恭、王振鹏、书法家鲜于枢,尤其是王蒙、吴镇、黄公望、倪瓒等人,俱从五代董源、北宋巨然、郭熙处淘洗而出,对赵子昂是无所依傍的。画坛的“宗主制”,实质上,在北宋文人士大夫加入绘画的行列后,已经开始震荡,到元代已名存实亡。
历史上,各画派的主要人物,在画法、风格上是不完全统一的。即使是董其昌的时代,各画派、画派代表人物的绘画风格,仍存在着差异。而差异的存在,是吸引人员介入、乃至重新组合的动力,也是确立画派形象,增强团队精神,提高画派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保障画派在市场有无强势竞争能力,能否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文人道统是重信义,重学术师承。对于吴门画派来讲,沈周被推为开创者,是不容置疑的。沈周的一生大抵不离苏州。明前期的苏州,一直处于朱元璋的政治高压下而饱受磨难。尽管明前期,在政治和文化上,有过一时开放的晴天。但苏州从未被“阳光”照射过。在其地的文人和画家,生活始终处于压抑状态,是没有什么作为的。文化只是一脉单传的存在。在此环境下,沈周亦无可能有特出的表现。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明宪宗成化末年(1487)的119年中,明社会的普遍心态是全面复古,大力倡导恢复中华文明,以铲除蒙元民族对汉民族的偏见和积习。政治上,朱元璋参照唐宋行政体制,制定和确立了国家的各项制度。在文化和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尊重文士,君臣和谐,礼乐修明,民风淳朴,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明初期,社会安定,社会心理积极向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各阶层整合的深入,朱元璋开始对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大清洗了。
朱元璋是位善用人才之人。他用人之长,经过十余年讨战征伐,力克群雄,建立了明王朝。然而,当年的才俊人物,现在已位极人臣,他感到危险就在身边。于是,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巩固自己统治的中央集权措施。同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杀戮功臣。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古训,还是要勤求的。否则,像刘基、徐达、胡惟镛、蓝玉……都是朱元璋原本倚重之人,尽被其铲除;右丞相胡惟镛以谋反被诛(1380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蓝玉谋反案(1393年),被勾连族诛者达1.5万余人。在朱元璋的尽情杀戮下,“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在意识形态上,由元入明,朱元璋奉行“制国当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使文人们深切地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然随着以诛杀的方法、整顿吏治的深入,朱元璋也由初始对士人的防范,转入大兴“文字狱”,滥杀士人。其对江南文人的打击尤为残酷,“吴中四杰”有三人被迫害致死。在绘画方面,就有赵原、徐贲、陈汝言、周砥、王蒙、王行、盛著、杨基、宋燧、高启、周位……被迫害致死(清初徐沁《明画录》)。这些人大都是苏州或寄寓苏州的画家。
“天下才子出江南”。江南才子当其时,大多活跃于吴中地区。同苏州有情分的许多画家,亦被诛杀。苏州在元末位居全国绘画中心,其地位是由高邮王张士诚兄弟对文化、艺术的资助所取得。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在苏北高邮称王。他与朱元璋一直处于鏖战状态。期间,朱元璋的心腹爱将胡大海被人杀掉,其人被张士诚所保护。以朱元璋、胡大海感情之深,使朱对张的仇恨达到了极点。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苏州为朱元璋攻克,张士诚自尽。然而,张士诚占据吴中时,在废除元朝苛政、兴水利、赈灾民、开宏文馆等方面很有建树,同苏州地区的文士和平民关系甚为融洽。苏州的文士、民众很怀念他及其家人。朱元璋对张士诚这个重要据点,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予以严厉报复和打击。诸如对富豪籍没财产,并将他们徙往内地;对民众增课税赋,如田赋,动辄以百万、二百万计,很是残酷。画家徐贲被腰斩,王蒙下狱而死,是与他们担任过张士诚政府职务分不开的。
吴门文士,大多在“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的社会心理支配下,纷纷转向“隐逸”。大批文人画家,承绪宋、元文人画传统,以画抒情、养性和追求自我意境的玩味。他们的活动范围,仍是以苏州为中心,仍很活跃;诸如杜琼、刘珏、谢缙、姚绶、沈贞吉、赵同鲁、沈恒吉。其他如龚开、郑思肖、张逊、柯九思、陆广、陈植、苏大年、朱敬重、觉隐、王中立、张羽、赵原、宋克、杨基、陈汝言、周砥、姚广孝、徐贲、王绂等人,都在吴中地区。
吴门画派是受浙江画派、元四家、南宋宫廷画风、北宋文士画风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赵同鲁、沈恒吉、杜琼一脉开导“吴门画派”的先声。
浙江画派是在明初社会全面复古的风气中,以复兴南宋院体画风成就突出、影响广大而形成的画派。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画派。
浙派的画家主要活动在杭州地区。南宋旧都杭州的绘画,一直是以南宋院体画风为主流。浙派的画家与宫廷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戴进为其开宗立派,在明初占据绘画的主流位置80余年。从其学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夏芷等人,然无大作为。至明弘治、成化年间,方由吴伟振兴“浙派”。 吴伟和沈周、文徵明等人同时,他的艺术影响力在当时极大。其弟子有张路、蒋嵩、汪肇、郑文林、史文、李著(本师沈周,继转吴伟)、彭舜卿、陈子和等等。戴、吴用笔,中侧锋并施,使转放纵,气势夺人。沈周就曾多次且时间跨度较大的临学戴进的画作。然浙派末流的创作流于草率支离,缺乏内涵,竟至萎靡碎弱。吴门画派应运而生。
明朝中期,随着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扩大,统治者对文化政策的放松,人文荟萃的苏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逐渐兴盛起来。文化环境上,苏州是文化诸多产业的贸易中心。其次,经科举入仕做官人员大量的增加,政治地位大幅度提升。再者,苏州位居水运枢纽,陆路也发达,是江南各地人才交流、书画收藏中心,吸引了各地文人纷纷迁至苏州。如此,均是缘于吴门兴盛的文风。
浙派的衰微,虽说有着诸多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了赞助者。随着苏州城市经济兴盛、新兴市民文化的兴起,南京文人圈亦开始钟情于苏州文化。艺术赞助者,大多是依文人对绘画品格的评鉴,来选择自己的投资对象。随着南京赞助者的兴趣转向苏州,浙派绘画在南京逐渐不受欢迎,其衰微也在情理之中。
吴门画派继承了文人画、院体画和浙派的画法,表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地区的城市风尚、市民意识和文化趣味。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人。自幼从元末经学家、画家陈汝言之孙陈宽、赵同鲁等人学习诗文书画。他的父亲沈恒吉从陈宽之父、翰林检讨陈继游学。他的祖父沈澄与陈汝言交厚,两家有三代师学之谊。陈汝言与王蒙、倪瓒交厚。沈家通过陈家交谊了许多元末以降的文人画家,收藏有董源、黄公望、王蒙的作品。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就曾经被沈家收藏过。王蒙为沈恒吉作画,想也不会太少。而陈、沈三代人以及杜琼、赵同鲁等人,都是过着隐逸的生活。沈周对文人画作风的继承,是家世作风熏陶之必然。
沈周天资卓绝,若天授。11岁时游南京,“上巡抚侍郎崔恭以百韵之诗,面试《凤凰台赋》,援笔力就……其文翰晖映,论者谓百年来无过者。”他擅长写生,山水、花鸟备其形态,间或草草点缀,亦能神气十足。其每画一轴,往往题以数十百言,文采风流,照耀一时。沈周的山水画分“细沈”和“粗沈”。世人多以“细沈”为难得,而“粗沈”乃是他性情本色作品,反不为人特重。“细沈”的代表作《庐山高图》,是沈周41岁时,为其师陈宽70寿辰所作,是他以王蒙画法所作的惟一巨幛,也是他标名画史的定鼎之作。
《庐山高图》用笔缜密而松动,画面细秀而明朗。画取黑龙潭瀑布、五老峰、苍松、丰华的夹叶林、奔涌的云海,表现性的图释陈宽明朗的人格。又以古风唱题:“庐山高,高乎哉!郁然二百五十里之盘踞,岌乎二千三百丈┉┉白发如秋蓬,文能合坟诗合雅┉┉公乎浩荡在物表,黄鹄高兴凌天风。”长诗以沉稳的笔调,激昂的情绪,为人们铺陈出庐山的可居、可游,其师品德可赞扬的、浩荡的艺术氛围。
沈周的本色作品,是用笔粗放、硬朗的一路。这些作品粗看上去,似有林泉高致的心境。然咀嚼一阵子,就感到其少却了清远的逸致,有点肉骨凡胎的味道了。想元王蒙最为浓密重厚的绘画作品,亦清气跃然。眼格于其作品、随神思其游走,你就会透过王蒙浓密的画面、深邃的表象,感触到他清廓、坦白的内心世界。沈周所图之景、所抒之意,少却元四家“泉石膏肓,烟霞固疾”的心性。从另一角度讲,也是沈周以绘画谋稻粱的结果。稻粱需谋,谋取必须有度,其程度如何,都表现在作品的格调上。如果你是画家,不暇让人从文人的角度观察,那什么事情就简单了。但对沈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割舍了“无聊”味道的作品。
沈周以一流的骨法用笔,间或一流的山水境界,创作出的一流作品不是山水,而是花鸟画。
他的花鸟画有工细设色者,出自南宋院体。有水墨写意者,出自文人传统笔墨,稚拙通透,情态洒脱。此得力于学黄庭坚的书法功底,能纵横、恣肆不够。以书法的创作状态、画山水的方法“写”花鸟,表现对花鸟情致的感受,使其作品平添了许多稚拙情趣。而这种效果的取得,要在他书法用笔虽刚狠,但能平稳。自然适于心意地“写”作,便有文气,也得静气。他的花鸟取材较宽,诸若白菜、大蒜及其它日常果蔬,均能信手拈来。在他之前,文人画多是以梅、兰、竹、菊为表现主题,少有人涉及于此的。尤以水墨大写意花卉,最能得意。其融会贯通的能力也是少有,在旧有的技法系统中,阐发以写为主的、新的表现手法,对后来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虽则如此,我们换个角度品评他的花鸟画,可看出其意气是飞扬不起来的,落实在书法上亦是如此,恣肆不够。他这一系统的花鸟画作者,能飞扬并独开生面的是陈淳。后有徐渭意气风发,高蹈激烈,狂放不羁,然同他基本不搭界,可叹!
沈周家世清高,学识广博,温雅宽厚、奖掖后学地品格高尚,人格近于完美。史传的东西,尤其是佚事记载,多有演绎的成分。诸若沈周对造他假画的态度,凡遇上门求题跋或署名者,皆予以大度的相助。以沈周清高的脾性,除非友人间互为笔墨。否则,这种可能性不大。
观他家世有鉴,在走进社会伊始,他的内心世界对社会诸多事功已失去兴趣(原本就不存在/或死掉了)。他一世地努力,就是要士子们在心底认他为“高士”。他力求自己的行为每日都与“完美”接近。同时,他每日都在失去的,是艺术情感。这点感觉,是在玩味他本色作品时,对其画感到缺少鲜活性、生命旺力的注脚。

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璧,字徵明,长洲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簪缨的家庭。其父文林与李应祯、吴宽、沈周三位高士友善。他自小就从三位研习诗文、书画。《明史》有载:“徵明幼不慧”,且外表愚钝。表明他不是“神童”。但以前述三位贤者之所长,施慧于他一人,亦其生之大幸。数年间,他便“颖异挺发”,以诗文、书画知名乡里。及长,平日相与携游的有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人,皆为风雅不群之士,捎带文徵明,人称“吴中四才子”。其时文徵明在四人中,很大程度是以有风雅气的官家弟子角色做陪衬的。有《明史唐寅传》:“吴中祝允明辈以放荡不羁为世人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世人的讥评,有文徵明陪衬着,口舌也就留些情,一带而过。
文徵明官宦家庭的背景,注定他一心要走科举的道路,但屡试不中。看到身边的朋友均先后中举,他哀叹道:“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也。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固能成因,然他的才学其实难与祝、唐、徐等人相匹比。
官家子弟,自有强人三分的家世背景,他因有正德末年(1521),以岁贡身份参加吏部考试的理由,在嘉庆二年(1523),就有人推荐他以诸生身份入翰林院、授待诏,参加《武宗实录》地编写,时年54岁。以诸生身份居于翰林院,可谓居之不易。他时闻:“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这话极是伤面子的。当此之时,又逢“大礼议”事。推重他的翰林院修撰杨慎,有明第一权相杨廷和的儿子,因在嘉靖三年(1524年)7月15日左顺门领头跪门谏争而失势。直接受到打击的有二百余人,其中134名五品以下官员被逮捕。后夺四品以下俸禄,杖五品以下官员180余人,17人被杖死。杨慎若非有家父倚仗,其结果不可设想。杨慎的失势,使文徵明居京城、谋发展的希望化为泡影。更有意思的是借“大礼议”而发迹的张璁,却是文徵明父亲的弟子。他虽不愿与张璁交往,但他父亲却未必不欣慰。
文徵明58岁时辞归故里。尝感怀到:“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 使人们看到他托身于仕林不得意的无奈,干青云之志的泯灭,被迫脱走的沮丧情景。也正是由于不满和无奈,才有了“洒脱”地“一笑”,吴门画派才有了自己的领袖——徵明文待诏。
文徵明的画“远学郭熙,近学松雪”。师于沈周,深谙王蒙、吴镇二家法。他对书法自晋唐以降,致力的功夫尤其多,自家书法面目清朗神俊。有书法了得如此,运用到绘画创作上,其作品中溢出的书卷气很浓厚。加之他的身世与环境的熏陶,其书画又具足富贵气。他有着重于时的诗文,有儒雅的气格和清贵的家世,当品评其书画时,所谓文雅神采迈越沈周,当然不是虚誉。随着同辈唐、祝这些不世之才的相继谢世,文徵明以长寿和资历,无可争议的主盟了吴中风雅30余年。
文徵明于书法、山水、人物、花卉无不精能。将他与沈周的研学与创作过程相比较,就可得出与画史所评,如晚明徐守知以及现、当代的说法者,即吴门画派是以“变元化宋”的观念来指导创作的高论,有所谬误。我认为当修正为“变元化宋”和“变宋化元”二种路数。二字相移,体用不同,差异亦大。
沈周,初以元四家入手,是家长的指导,或勉为资质高明。是以元四家入手, 创作手法在当时属写意一格。但是,元四家的画法,是在遵循了唐、宋画法规矩后的写意。沈周学元四家后,才意识到唐、宋“规矩”二字,是后而知之。即使如此,他并未认真的对待唐、宋人,而是下了很大功夫学习浙派画法。他54岁时还在临戴进的作品。临当代人的作品,一是材料,二是技法,三是气息,四是手感相通,便捷实用,能很快上手。他58岁后临北宋燕文贵,古稀后临刘松年、李唐等十六家的山水画。虽如此努力,其本色作品尚不免“粗”,时或犯俗,少却古淡雅健的韵味,一生未脱却刻露的味道。这点遗憾与他卖画为生有很大干系,但更为主观的看去,是天性使然。他年青时,对元四家高邈的东西,就未参透。有以为证:“又过矣,又过矣”。赵同鲁对其学倪瓒不得简旷清润意旨,多次予以批评。他学王蒙画法最佳的《庐山高图》,张扬的是“丽”字。我不是说他没有浓郁的调子,而是说他欠缺盘礴的深意。 “变元化宋”,此虽是一路,但吴门弟子不与之同。
文徵明画以宋郭熙、元赵子昂入手。郭熙是北宋宫庭画家,著有《林泉高致》,是中国美术理论史中,阐述山水画技法题材与创作体裁和艺术思想的经典论著。赵子昂的画是由士大夫感怀所寄表出的东西。他对李成、郭熙的画法捻熟的很。二人都有工谨与放开手脚的作品,供他选择。他学元四家,深得王蒙(赵子昂外孙)画法三昧。他以宫庭画法“写”意趣,将王蒙的幽深绵密发展到极致。于青绿重彩山水,也以“写”得秀雅文致。至于世说之“粗文”更得文人喜爱,画面轻松,“松”则“气”易焕发,是世风所好,不是文徵明的专长。他是“变宋化元”的路子,笔墨清秀,气息雅正,不刻露,为吴门画派主导画法之一。

唐寅(1470-1523年),字子畏、伯虎,晚号六如居士,吴县人。董其昌云:“唐伯虎虽学李希古,亦深于李伯时,故人物、舟车、楼观无所不工……正、嘉间,吴郡士大夫作画之人,无以胜数,而六如第一。”黄质公语:“画山水人物无不臻妙。原本刘松年、李希古、马远、夏圭四家,而和以天倪,运以书卷气。故画法北宋者,皆不免有作家面目。独子畏出,而北宋始有雅格……家吴趋里。才雄气轶,花吐云飞。先辈名硕,折节相下。”其人物画造型头部略阔,身材略窄,有弱不禁风之趣。面部之额、鼻、下巴等处,以白粉稍加点缀,设色的方法直接继承唐人,如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又纳入李公麟行云流水般的笔线,有弹性,有风味。人物群组合,以二维半构成,有形式感、装饰性。对明、清的其他画家影响很大,如仇英、陈洪绶、禹之鼎等人,只是陈洪绶夸张表现的程度更加深广。纨扇仕女画,尤为文致。他笔下的仕女,表情稚拙,柔意幽婉中透出庄重。水墨写意人物,性格明朗,解衣之际迭散着雅逸。
他的山水画,是以人物为力量的中心,突出的是人物,是人物画成就了唐寅。在严格意义上讲,他的创作始终是以人物为中心,山水为辅助,或说是补景来处理,山水画在唐寅那里,不属主题创作。这是吴门画派研究者,需重新认识的问题。
唐寅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苏州府学。日夕与祝允明、徐祯卿、张灵等相切磋。他性格热烈开放,经常与张灵纵酒游乐。自由奔放的个性,使府学教师们很无奈。他的父亲亦叹道:“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寅15岁至25岁期间,对科考之八股文不屑一顾,而钟情于古文。这表明他成为秀才以后,对进一步的科考无大兴趣了。然而,促使他重新进取科考的原因是:他25时,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他深切地体味到了人生苦短,感喟出:“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他开始谋事举业,并对祝允明人等放言:“闭户经年,取解首易如反掌耳!”直是数百年才出的一位人物。一年后(1498年,29岁),他赴南京乡试取第一,得“解元”,声名远震,惹得许多官员争着要收他为门生。次年,北京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是极为欣赏他的,博取大功名对唐寅来说,似为囊中取物。不幸的是,同他结伴赴考的同乡徐经、行贿主考买题。事发,程敏政、唐寅等人俱受牵连。唐被逮系诏狱,严刑拷问。及案情明了,功名亦被革除,派往浙江为小吏。唐寅拒不赴任。他用的是中国文人最后的一招,那是自尊,可以阻断一切妄念的一颗文心。中国文人用的这一招,多数是属无奈的自残。
唐寅回到家乡,兄弟与继室皆耻之,而“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皆指而唾辱亦甚矣!”他遂以“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 的态度,20余年,以茹苦的心灵,过放浪的生活。其用印“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孤苦的心灵,积郁的愤懑,狂放不羁的举止,都包含在自嘲性的印文里。诸若“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这种近乎直白的诗句,在一般士人吟咏起来,我会想到“酸腐”二字。但出自唐寅口中,就显得平实。这是唐寅人生价值的取向?是他的“心死”了,是哀莫大于心死的表征!他浸淫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六如居士凄凄婉婉:“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署《伯虎绝笔》。作为才学超绝的文人,其下场是悲惨的,让人唏嘘不已。我们的历史,记载着太多的文人悲剧。然而,更悲惨的,是那些在历史上没有传载的人。史书已经为唐寅的诗文书画及其韵事费了许多笔墨,他真是太“幸运”了。

在考订吴门画派人员组成上,今人惊诧于莫名的,有诸多的言论,不愿将唐寅列入吴门的文人画派,这是脱离史实背景的。我思前想后,大致想到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出生于商人家庭,曾过着“居身屠酤,鼓刀涤血”与屠户、小贩为伍的生活;二是他科举受挫,虽无大干系,然名节大损;三是他与当时文人目为画工的职业画家过从甚密;四是他虽师沈周,实师学于周臣。宗法的是浙派、南宋四家等等。这些口实,使那些人以狭隘的、龌龊的心理对待唐寅。想中国文人史中,论文采风流,有多少人能盖却伯虎?吴门画派能形成气候,在极大程度上要仰仗唐寅的声名。没有他鼎力合作,有吴门画派吗?就别讲在画坛称盟主了。
唐寅对中国画史(包括文人画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文人的情怀,创造性的将书卷气注入宫廷画的图式。关乎文士所有要具备的气质,在他那里均能高蹈而出,而且是飞扬的。这在他之前、之后乃至当代,有多少人能与之共舞?
若论起仇英,几乎被人无余地的目为“工匠”而从吴门画派中剔去。其实,若深究绘画艺术的创作,无论何派何家,其元创时,尚有意义,诸若文人画。至后纷纷来者效仿,与画工何异?像现代黄宾虹,学之者,徒然为其形迹,实在黄家技法中讨生活,其有几人淘洗得艺术精神?文人画派史中没有仇英,比唐寅更惨。倒是董其昌挺会说话,因前面说了沈、文为“第一”。谈起仇英,他在题《仙弈图》时说:“仇实父为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又“五百年而有仇实父”。直若孟子五百年有圣人出之说。按此,仇英至少是画中亚圣。

仇英(约1498-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他较文、唐小20岁左右,较沈周小70余岁。从吴门画派发展地时间,递次人员关系上来看,他无疑是吴门画派“生物链”的重要环节。仇英于1518年移居苏州。约在1518年入周臣门下,称唐寅为师兄,研习南宋四家。稍后,又上溯唐、北宋谨严精密一格画法。他注重表现其生活时代的人物形象,画法工细精谨、赋彩清艳,风神蕴藉典雅。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藏家项元汴,邀请他寓居10余年。吴门画家文徵明、唐寅、沈周、祝允明、王谷洋、陆治、周臣……都多次与他合作书画。其实,他们是从仇英那里讨生活。文士之间的交往,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否则不可能往来至深。仇英的“画工”名声,是坏在后人没有深解董其昌的一段话:“李龙眠、赵松雪之画极妙,又有士人气。后世仿得其妙,不解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实父!”有些人就是误解在“士人气”、“不能其雅”。明眼人一看,就知董其昌是讲仇英的画,既有士人气,还有妙和雅的韵味。而且,五百年才出这么一位。对董其昌的这段话,黄宾虹也误解,曾批评董其昌:“董思翁不耐作工笔画……”。耐不耐作工笔画,与“雅”和“士人气”无大关系。况且,董其昌称赞的,恰好是仇英的工笔画。高人尚且如此,无怪他人随附了。但是,这种观点贻害甚大,使人们误解为:凡工笔画者,都不属文人画范畴。清张潮《虞初新志》谓仇英:“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与唐寅有相似之处,对于他更纯粹的讲,是“出身”的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成名人士皆出于王公贵胄?狭以问老、庄是何出身?白石老人是何出身?孔子生身尚有考论,子嗣有几多高人?仇英生活的明中叶,承前期文化对唐宋的复古,其时兴佛、道与心学。人抵其学问不强的最大口实,是仇英不在画面上题写诗文。但是,若缘于当时的人文背景考问,他“不著一字”,诸般意画面已然示之,岂用文字解说?况且亦合于唐、宋及上古绘画无有文字题解的道统。由是一解。有《大观录》载项声语:“仇十洲先生画,实赵吴兴后一人”。赵吴兴是文人吗?这就足够了。吴门画派是以沈、文、唐、仇为核心的,志趣高尚的画派。他们的创作手法,以用笔坚劲而言,都涵富着宋人意味。稍有区别,无非是此近于元,彼近于唐、宋而已。但其所共具的气格,是由吴门地域文化氛围所培植出的,是其市民文化意识下的产物。他们作画的主要功用之一,是用于市场贸易,以为生计。中国文人画遵从市场贸易需求的意识,从规模与纯粹程度上讲,应以明代为始,是进步的开始。

明、清时期画派大量产出,画家数目之巨,是其以前的任何朝代无法相比的。清徐沁《明画录》载有各类画家800余人。清嘉庆时期,有彭蕴灿《画史汇传》载有历代画家7500余人。其中,记录明代至清中叶的画家达5500余人。在这么大的数目中,理清文人、宫庭的画家或者画派,无疑是难以确指的。然自文人画兴,上自朝中王公贵族,下至布衣文人组成的、庞大的画家群体,将宫庭绘画排斥在主流之外,由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代替,而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在明代,各地域和各个有独立创作能力的人,在求新、求变、求悔的社会心理下,人人乐于学术标榜,积极突显自己的个性,各种文化社团繁盛。吴门画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主盟画坛近百年。
综观上述说解,是对过去人们对画派组成人员的划分,存在风格、地域的争执问题,给予的试言。画派当以地域分,以风格分。具体如何去分,就需要贴切于史实背景了。如此,以董其昌为界,其前种种,应按地域分。其后种种,应主要按风格分(亦含地域)。二者是交叉进行的、互补的。前之所以混淆不清,是由理论大于实践者,不体贴画家,漠视史实所造成的。复也难怪,诸家品评艺事,首重的是对艺术风格与精神的界定。
鉴于吴门画派从人很多,仅画史注册的就有几十位,对后世影响与衰落,牵涉诸多方面的因素,待后续文。
(文/魏广君,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京华印社社长,一级美术师,原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杂志,来源:京华印社官微)
